李向平:佛教中国化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变迁来说,"中国"的概念拥有多层含义,最初是一个居住地域、空间方位的定义,继而是政治中心即都城的象征,接下来还有文化、民族、国家体系的意义生成。这一历史文明的变迁说明了"中国"的概念也是伴随中华文明历史的演进与拓展而逐步延伸出来的,空间、国家、文化、信仰方式等等,均为其中基本内涵之一。
当代中国佛教、中国宗教的中国化理念及其理解,就中国概念的逐步拓展和方法的发展历史而言,实际上也是一个演变和丰富的历程,尤其在中国文化演进历程之中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佛教,它的中国化模式同时也是一个丰富而漫长的形成历程。千百年来,汉文《大藏经》及一部《中华大藏经》的形成历史,无不充分呈现了佛教在中国、继而中国化的精彩历程。汉文《大藏经》作为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国化、中国化佛教的主要载体,一方面是能够"外化其形",同时亦能"内化其心",先后在语言翻译、思想格义、译本刻写、文本建构、结构完善等不同层面,充分展现出佛教、中国佛教、佛教中国化的价值观念和中华佛教文化的独特魅力。
今读纯一法师大著《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以汉文大藏经为中心的文本研究》,从《大藏经》的语言翻译、译本刻写到佛教文化嵌入、藏经文本集成、体系编撰及其结构体系的独特视角和论述方法,深入经藏而重新审视、解读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国化的精彩历程,设计,佛教中国化的精彩历程,请佛教文化嵌入、藏经文本集成、体系编撰及其结构体系的独特视角和论述方法,深入经藏而重新审视、解读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国化的精彩历程,以佛教文化嵌入,为佛教文化嵌入、藏经文本集成、体系编撰及其结构体系的独特视角和论述方法,深入经藏而重新审视、解读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国化的精彩历程,以佛教文化嵌入,为佛教文化嵌入、藏经文本集成、体系编撰及其结构体系的独特视角和论述方法,深入经藏而重新审视、解读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国化的精彩历程,请显示佛教文化嵌入,为佛教文化嵌入、藏经文本集成、体系编撰及其结构体系的独特通过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勾勒、展现、论述、证明了佛教中国化之文本结构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的具体贡献,条分缕析地论述了自印度到中土之后2000多年佛教之中国身份的文本配置及其知识体系,诚为当下讨论"佛教中国化"论域中的重大言说,颇值一读。
一、文本研究法与《大藏经》中国化
文本研究法是指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主张凡是与文本有关的内容都纳入到对文本意义的梳理与讨论之中,如通过对文体、作品风格、时事、地理、风俗等全方位的论述,最后实现对该文本的全面剖析,以深究的文化文本价值。但是,像佛教《大藏经》这样一项文本的形成却是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而不断形成的。
纯一法师的新著恰好就是以汉文《大藏经》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文本集中加以论述,视文本为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实现路径,紧扣《大藏经》文本之研究。这样一种研究视角,正是基于佛教文献学研究的固有论著,同时把佛教文献视为佛教中国化的深层结构,视为佛教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或文化结晶。具体而言,即是包括佛教来到中土之后的各类本土著述、本土编辑及其丰富的中国内涵,如何呈现在《大藏经》文本结构、《大藏经》编撰体系及其分类法的中国化,最后促成《大藏经》结构体例的成熟,呈现为佛教中国化的文本特征。
正如纯一法师指出,"佛教中国化是一个过程",这就好像汉文《大藏经》文本结构具体形成过程那样,《大藏经》作为中国文化思想革命的产物,既是编撰汇编的结果,更是中华文化再生产的历程之一。因为文本叙事乃是人类文明活动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会充分展示一个文明体系中的意义结构如何通过文本叙事而被组织起来,成为统一的神圣结构。因此,在汉文《大藏经》的文本研究过程中,纯一法师条分缕析,经由汉文《大藏经》的翻译、格义、译场、民间刻本、官方刻本等方面的梳理,乃至对汉文《大藏经》的各类作者、读者、视角、评论等方面的述说都为此产生了新的意义与象征,进而把《大藏经》文本视为研究佛教中国化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分析路径,将为佛教中国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建构一个新的研究天地。
二、从佛经中译到中国文本类型
一般而言,文本分析法主要包括有文本形成的序列分析、文本类型分析以及文本结构分析。特别是文本的结构分析之中包括了文本结构中的各种话语序列、文字类型、意义象征、历史关系,同时把文本的结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展示给当下,具体说明该文本的结构主体,何以为文本研究之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与影响,此中包括文本结构形成的基础、特征、核心问题,如何呈现为某种文化影响。
正是基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考量,纯一法师在其新着中的文本分析与论述,实可帮助读者再度打开汉文《大藏经》佛教经典丰富博大的精神世界,深入《大藏经》内部结构,并且从对《大藏经》文本本身的关注,深入《大藏经》文本所承载的社会历史内容,促成人们回到文本本身,使经典阅读更加完整。
在此文本结构之中,纯一法师对于《大藏经》文本结构的主体把握得十分准确,这就是中国僧人著述作为汉文《大藏经》文本结构的主体,同时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僧人的著述可谓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进而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远大历程。
最早的佛经翻译,始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东汉——初创翻译时期,东晋与隋代——官方翻译时期,唐代——全盛翻译时期,宋代以后——刻本翻译时期,自宋以后佛经翻译逐渐减少,并因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迅速提高佛经的印刷和流通速度。佛经中译前后历时约10个世纪,共译佛教典籍2100余种、6000余卷,著名中外译师不下200人,其中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人为"四大译经家"。
在佛经中译的过程中,中译文本的进行与不同写本、刻本的结集问世,乃是佛教文本中国化重要构建者的角色。从民间译经到官方"译场"的出现,从西域僧人主译到中国僧人监掌译事,使译经体制逐渐由小规模的个体活动向有组织、有计划、分工明确、机构宏大的翻经馆的形式发展。直到宋代译经院的制度更加完备,译经制度与译场分工,随着译场的出现,译经制度也日益完善。翻译一部经需要九个职位密切协作。很明显,上述这些官办与民间创办的译场,不仅是翻译佛经的场所,也是佛教教育和学术交流的场所。中译的佛经、中国人编辑的写本与编撰刻写的各种刻本,渐渐建构了佛教中国文本在中国的身份。
上述历程是大量的佛经译本、写本、官译、官民共建的文本建构历程。自汉至隋唐,佛教典籍的文献流传主要依赖于写本。自东汉翻译佛经之始,即有写经,如译成之经文大多由笔受者直接书写下来。而佛经本身也强调,信徒诵读、持带、转赠、抄写佛经,是一种重要的功德修为。之后《大藏经》文本结构的逐步形成是基于各种写本、刻本、官刻与民刻两大文本,直至近代印刷本等文本形式的出现,以及文本知识结构、体系的演进。
基于这一观念,纯一法师认为,随着译经的增多和佛教的广泛传播,中国佛教学者留下了更多自己撰写的佛教经典著作,包括章疏、论著、语录、史传、音义、目录、杂撰、纂集等。它们都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也是把握中国佛教与中国文本的关键。由翻译而来的佛经与中土著述所形成的文献,是佛教在中国得以广为流布的最重要传播方式之一。作为文献媒介的文字和载体让异时、异地的传播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佛教传播的广度和范围,而佛教典籍在中国的流布经历了"佛经汉译—经录编撰—《大藏经》刻印"这一文本的传播制作过程,一方面证明了佛教传播的中国速度和中国范围,一方面展开了佛教在中国、佛经中国化的漫长历程。
通过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汉文藏经各种译本与写本、刻本的演进,不仅给汉语言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比如世界、平等、慈悲、未来、地狱、秘密、以及三世观念、因果轮回、三界六道等词汇,都是译经者通过意译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同时通过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的影响,大大拓展了中国价值结构、文化想象世界,首先就奠定和丰富了汉文《大藏经》文本的意义与象征,从而呈现了《大藏经》汉译及其写本、刻本形成中所呈现的中国文本类型。
因此,"佛经翻译与解释的中国化"、《大藏经》文本的刻写方式及其文本类型之中国化,此乃"佛经中国化的基石或根基"。汉文《大藏经》的官刻本、私刻本、民间刻本,官方资助、从民间译经到"译场"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藏经文本中国化的不同体现形式而已。
三、汉文《大藏经》的文本类型
在汉文《大藏经》的中译历程中,因为各种译本和译本结集、刻本的不同类型,形成了汉文《大藏经》中国化过程中的不同文本类型。与此同时,是中国僧人的各类著述,纯一法师称之以"中华著述",它们共同组成了汉文《大藏经》的翻译类型学与汉文《大藏经》的文本类型学。
《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一书认为,中国人创造的"大藏经"一词,"既吸收了印度佛典管理的内容,又融贯了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本身就是中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就汉文《大藏经》的内容而言,可分作"翻译佛典"与"中华撰述"两大部分。其中,"翻译佛典"不仅包括经、律、论三藏,还包括西土先贤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既包括从梵文、藏文、巴利文翻译的经典,还包括从中亚一带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经典,内容涉及大小乘、显密教等许多部分。而中华撰述部分均为中国人的著作,其最为著名者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唯一称为"经"并流传后世成为中国佛教重要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资料宏富,构成了汉文《大藏经》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汉文《大藏经》的抄本类型。依据纯一法师的梳理,印刷术尚未发达时,写经实具有弘传流通之意义与功德之意味。由此,大规模、长期性的佛经抄写行为得以开展。在此类文本类型之中,除僧侣与官府有组织的抄经活动外,大量的信众也加入到抄经行列之中,有的为发愿,有的为布施、祈福,有的为超度亡灵,或为做功德。之所以能够出现如此丰富的手抄文本,这是因为崇德报功的中国信仰传统与"书写法事"、抄写经文紧密结合,成为"五种法事中功德最殊胜者"。
可以说,供养经卷是汉传佛教在译经过程中逐渐把佛教信仰中国化的一大途径,作为一种法事供养,它带有中国儒家重视文化书籍的内在影响,并与佛教结合而将抄写佛经、绘制佛像作为修行的一种功德,以捐献数量多少为虔诚程度的标志,这就促使抄写经文作为民众表达对佛教信仰的一种普遍行为,从而使汉文《大藏经》进入中土之际就与汉民族的传统信仰结合起来,构成汉文《大藏经》最能中国化的神圣底色。
再次,是刻本《大藏经》的发展与演变。佛教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佛教的一些佛像和经咒都是早期的雕版印刷物。纯一法师在书中说道,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就是在我国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然而到北宋中叶之后,雕版印刷术已风靡全国,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是空前未有的。因此,在唐及五代佛经的印刷还只限于单卷佛经及佛像,到宋代则出现佛经总集的刻印,刻本《大藏经》时代已经到来。据统计,宋代至少进行过6次佛经总集的刻印,这就是《开宝藏》《毗卢藏》《资福藏》《圆觉藏》《崇宁藏》和《碛砂藏》等。其中,《开宝藏》为朝廷所刻,作为中国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经》,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木刻大型丛书,它开创了刻本《大藏经》的先河,是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在此基础上,手写佛经逐渐减少,官私刻印藏经的风气渐开,契丹、高丽、福建、浙江等雕印《大藏经》也都深受《开宝藏》影响。从此,中国佛教典籍的传播有了可以规模化刻印的定本,对汉文《大藏经》刻本类文本的形成与传播居功至伟。
当然,在刻本型文本的《大藏经》之中还有不少民间私刻的文本类型,比如北宋时期我国第一部民间私刻的《大藏经》——《崇宁藏》。它由福州东禅寺等觉禅院慧荣、冲真等发起劝募雕造,初名《大藏经》。它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由寺院发起募捐的方式集资刻印的《大藏经》,开创了我国私刻版《大藏经》的先河,其版式对后世《大藏经》刻板影响甚大,其后的《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等7种版本《大藏经》,都按此版式刻印。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间私刻的《赵城金藏》,多达7000卷,施资者主要是山西晋南各县的村民,全靠一个地区的百姓出资。由此可见,官刻与私刻的汉文《大藏经》文本同为佛教文本中国类型建设路径之一。即便是到了晚清民初,著名的佛教居士杨文会也是以民间私刻文本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在这里,读者不难体会纯一新着之独特与别致,佛教中国化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既有官方主导以文化建设为特征的文本意义,亦有民间作为崇德报功象征仪式的中国化寄托,更有些汉文《大藏经》文本类型是民间信徒募资刊刻、官方高度认可,官民共同合力完成,其丰富的中国意义象征皆能包含在汉文《大藏经》的文本建构之中。如我国古代刊刻的最后一部官版《清敕修大藏经》,亦称《龙藏》,也是充分借鉴了明代官刻《永乐北藏》和民间私刻《嘉兴藏》的文本类型。再有就是1982年启动的《中华大藏经》编辑整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之力支持学术界整理编辑的一部汉文《大藏经》,其正编就是以民间刻本《赵城金藏》为底本进行影印,其缺失部分则由《高丽藏》补足。纯一法师的精当论述,说明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多样化及不同路径的中国化,方才得以建构了中国佛教的博大精深。
四、汉文《大藏经》的文本意义
汉文佛教经典在中国的流传,经过历代的翻译以至汇集、编次才逐步形成完整系统的《大藏经》。在此过程中,佛典目录对《大藏经》的收经标准、分类体系以及框架结构的形成和定型起到了重大作用。它是佛教中国化文本类型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纯一法师在《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论述道,智升所著《开元录》集前代之大成,乃是汉文佛教文本结构走入体系化阶段的象征。唐开元年间(713-741),佛经中译事业告一段落,长安西崇福寺僧人智升通过辨伪存真,去粗取精,撰写出反映盛唐中国佛教发展水平的目录学著作《开元释教录》,进一步完善了此前的佛经文本的分类方法,随之确立了汉文《大藏经》的文本结构,即《开元录》所立"有译有本录"之下的编目体系一直成为后来中国所刻藏经分类编目的主流,千年流传不替,成为我国历代《大藏经》结构体例之圭臬。
这种文本分类方法,促使中国佛经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时期。至《开元释教录》,则为卷喜爱浩繁的佛典排定了在《大藏经》中的次序,使得后世汉文《大藏经》有了一个普遍遵从的标准,为以后的《大藏经》雕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此,我国汉文《大藏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基本统一,最后确立汉文《大藏经》文本结构的基本格局。
为此,我们不得不非常认同纯一法师的这一重要论述:层层叠叠构成的汉文《大藏经》,既是一部"经典传译史",也是一部"思想诠释史"。它们源于中国化佛教信仰的流传方式与功德积累方式,同时也基于汉文《大藏经》这种独特的文本类型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对于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变迁而言,中国化这个概念,原来是如何完成、实现从印度到中国的一个地理空间概念,历史事实却因汉文《大藏经》的建构与完成,使"佛教"已经建构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文化概念。
传统的佛教中国化及其文本类型主要在于"翻译佛典"与"中华撰述"两大层面,那么,当代及其日后的佛教中国化使命,可能还有如何建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这就是该书作者第六章的主题:《大藏经》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塑造。面对这一历史使命,中国佛教应该何为何,有何承当?对此,纯一法师此话一语中的,那就是"践行菩萨道,复兴中国文化"。
纯一法师从2006年就开始参与整理点校汉文《大藏经》的工作,带领团队完成了《中华汉文大藏经》的经目考证以及目录编撰工作。从学术的视角出发,在采纳被称为"现代以来佛典分类最新成就"的《大正藏》基础上,这将使《中华汉文大藏经》目录的分类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善的。
依照纯一法师的宏大悲愿,汉文《大藏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应该是采用古籍整理学的学术方法对传统的汉文《大藏经》进行现代化的整理,即用校勘、标点、注释、辑佚等方法进行整理,以适应今人的阅读习惯,使《中华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目前收经最完备、版本最权威、使用最便利的现代读本,是汉文《大藏经》的现代化使命之一。
佛教文化早已融合到中华文化沃土之中,而已为沃土的中国佛教文化,如何养成中国文化之要义,如何构建一个当代的汉文《大藏经》文本,使之成为宏富的中国化佛教神圣结构,实际上也是"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江西的佛教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延绵数千里的崇山峻岭孕育了六祖门下一花五叶中的四叶六宗,中华禅宗的重镇,祖庭众多,高僧辈出,尤是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写下了中国佛教本土发展辉煌的历史篇章。纯一法师现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南昌佑民寺方丈,身兼数种要职,现身弘法于国内外,善工丹青与书法,近来又大着问世,发明于佛教中国化重大问题"诚有"理事圆融""一切现成"的古道禅风,唯有习静苦参,深入品味中国话头,才能感受纯一法师撰着汉文《大藏经》文本研究之慈悲情怀。
该文发表于《法音》2021年第1期,第17-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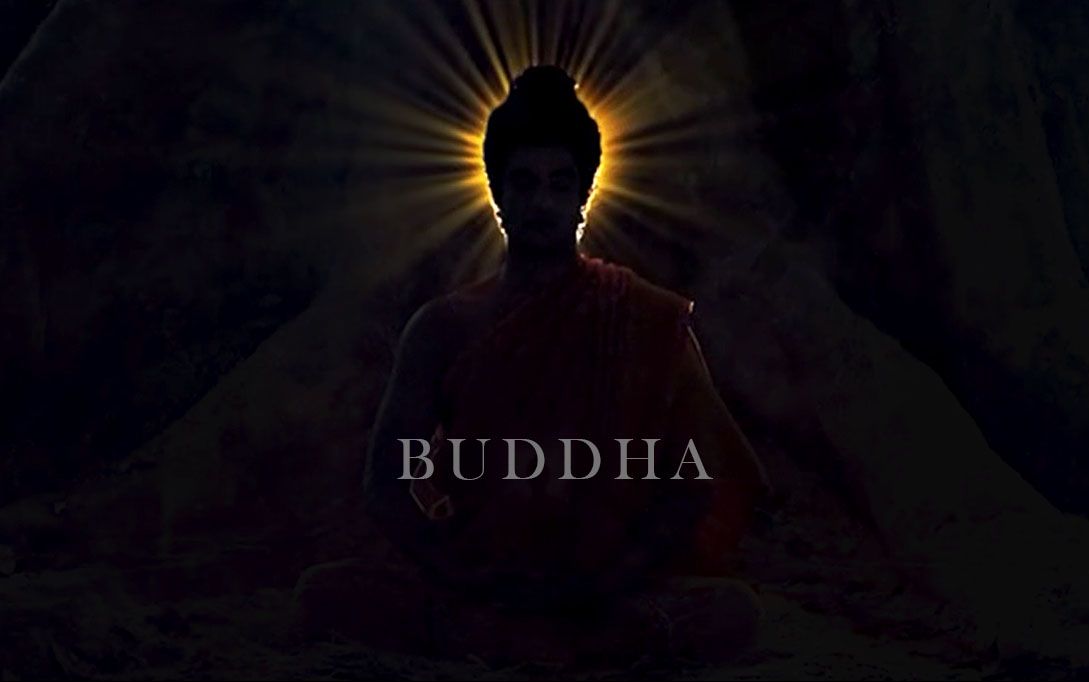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