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如法师:再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第二次佛教中国化略论
内容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宗教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中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在中国历史上,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已经第一次成功地中国化。然而,站在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佛教又将面临着全面地第二次中国化。中国佛教唯有成功地完成第二次中国化,才有可能全面融入当前中国大文化的创新,大中国的崛起,才有可能通过第二次中国化而真正走向中国佛教的世界化。本文以佛教中国化的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个支点进行论述:首先,对自道安法师以来中国历史上佛教的第一次中国化进行阐述。其次,论述了中国佛教在唐宋以后的衰落以及晚清以来的极度式微,以致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拉开第二次佛教中国化的序幕: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兴起。最后,笔者对未来成功创新的中国大文化进行了展望,对于未来中国佛教如何成功实现佛教第二次中国化提出三个基本要点。欠缺不当之处,恳请领导与方家斧正。
关键词:中国化、第一次佛教中国化、第二次佛教中国化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此外,习总书记特别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本文关注的就是佛教中国化的问题。
有关佛教中国化问题,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1995年就在《中国宗教》上发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认为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已经第一次成功地中国化。
在学界,有关佛教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既有单篇论文,也有专著。单篇论文的数量比较多,而相关的专著,比较突出的有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以及何锡蓉先生的《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双向建构》二书。至于单篇论文,有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如尹德蓉先生的《从历史演进论佛教的中国化》,方熔先生的《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路径》;有的则从典型个案的角度来考察佛教中国化,如方立天先生的《慧远与佛教中国化》,韩秉芳先生的《从庄严未来佛到布袋和尚——一个佛教中国化的典型》等;有的则从佛教中国化本身的特点、意蕴及发生的原因等方面,来考察佛教中国化,如刘曙东、农夫先生的《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意义》,孙九霞、马建钊先生的《试论佛教中国化的特点》;有的则从佛教的中国民间化、通俗化以及佛教僧尼日常生活的民族化的角度,论述佛教的中国化,如欧人、王世勇先生的《佛教中国化问题管窥》;有的则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佛教的中国化,如陶全胜先生的《佛经的翻译策略与佛教中国化》。这种多角度地考察和研究佛教中国化的方法,是与佛教中国化发生的全方位性、多层次性相适应的。而在这种多角度的揭示中,有两点最为关键,也最值得注意:一是对“佛教中国化”的准确界定,二是对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的揭示。对于什么是“佛教中国化”光是笼统地说佛教中国化是指佛教带上了中国的特征,这是显得粗疏的,因为按照这样的认识标准,那么,佛经的翻译也可算是真正的佛教中国化了,而由“格义”比附的方式产生的“六家七宗”,也该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了。但实质上这些都只是佛教中国化的初步阶段,离真正的佛教中国化还有一段距离。为了廓清对佛教中国化认识的粗疏之处,何锡蓉在其专著《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双向建构》一书中,结合僧肇与竺道生等人的阐发,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她认为只有像僧肇、竺道生这样在正确理解佛教原义的基础上,依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提出新的佛教见解,才算是真正的佛教中国化,因为这些新的佛教见解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的融合,而不再是初期阶段的那种浅层次的、歪曲比附式的融合了。这一佛教中国化的定义对我们界定何谓西方文论中国化也有启发意义。而关于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不少研究者都涉及到了,但是阐述得比较精当、清楚的是方立天先生,他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中指出“中国佛教哲学是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是中国佛教学者把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相结合的产物。”这句话,就清楚地把方先生考察佛教中国化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角度表达了出来,即他是从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等方面来揭示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的。总之,现有的有关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成果,较为清楚地揭示了佛教中国化发生的历史、内在机制以及发生的各种层面。而本文将依据上述相关研究,以中国佛教的过去、当前、未来为三个支点,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疏理,从而提出中国佛教第二次中国化的相关论述。
一、中国化的两种视角
在学界,有关佛教中国化的问题,最少有两种视角:一是“中国”化“佛教”,二是“佛教”化“中国”。
(一)“中国”化“佛教”——以道安为例
佛教的传入,必须适应中国本有的文化土壤、社会制度、风俗人情,特别是得到当时政权的认可,唯有这样佛教才有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以东晋道安大师指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可以说是推动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道安提出的这一原则核心是“依靠国家政权立佛法”即向佛教界提出了如何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种适应,要求佛教主动适应社会,接受国家政权的管理。也就是说,在佛教的管理体制上,他正在考虑中国化的管理方式。所以,“依国主,立佛法”的原则,实际上强化了佛教的社会性和政府性。佛教的社会性和政府性的特征,就是主张佛教的活动要与政权建设相协调。佛教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众,以此争取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支持。从而建立国家的权利与佛教大众的权利的互动关系。道安“依国主,立佛法”的主张,把中国儒家的“君臣”纲常关系融进了印度佛教。
此外,道安在理论上创立学派,兴起中国式般若学;在组织上建立了以道安为核心的释姓汉僧网络;在制度建设上探索了中国佛教的管理新路;在信仰上创立了一种适应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新模式。道安从各方面进行的改革,全面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
(二)“佛教”化“中国”——依牟宗三观点
就文化价值而言,如果佛教完全被中国同化,则佛教就已经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就佛教自身而言,无论如何变通外在的形式,而作为佛教最核心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是不能改变的,否则佛教如何被独立识别?是以自两汉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僧人不断东来,其核心目的,无非是为了传播佛法:即将佛教的核心方法论与价值观传到中国。是以牟宗三先生认为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其义理变化具有一致性,而所谓中国化的东西,都是表面迹象的不同。佛教“虽处在中国社会中,因而有所谓中国化,然而从义理上说,他们仍然是纯粹的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生命与智慧之方向对于他们并无多大的影响,他们亦并不契解,他们亦不想会通,亦不取而判释其同异,他们只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尔为尔,我为我。因而我可说,严格讲,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只是中国人讲纯粹的佛教,直称经论义理而发展,发展至圆满之境界。”“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都是一个佛家,它的不同……是表面那些迹象不同。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表面迹象的不同……就说有一个中国的佛教又有一个印度的佛教,好像有两个佛教似的,这是不对的。只有一个佛教。”既然所谓的中国化只是表面迹象的不同,因此从整体而言,中国佛教仍然是对印度佛教的一脉相承,佛教未曾中国化。
(三)小结:在互化中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与繁荣
事实上,在学界之所以有以上二种观点,也只是因为视角的不同:就“中国”化“佛教”来讲,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传播到中国,必然要适应中国的政权制度、社会结构和价值序列,以此视角分析,佛教必须要中国化,否则佛教何以在中国立足?是以东晋高僧道安高举“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积极全力推动佛教的中国化。而第二个视角是就佛教本身传播佛法的核心价值与目的来讲,无论佛教如何在中国,或主动中国化,或被动中国化,对于佛教僧团来说,其得以维系几千年延绵不绝的秘诀在于:佛教核心方法论与价值论的代代传递,这就是法身,这就是慧命。以此视角则佛教从来没有被中国化,而是将其核心的方法论与价值观传到中国,斯谓“佛教”化“中国”。我们可以假想:如果佛教传来到中国之后,被先秦诸子如儒、道、法、墨、兵法、阴阳等任何一家完整或彻底地同化,即其核心方法论置换为或儒、或道、或法等任何一家,那么佛教还有单独存在的意义吗?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还会有儒、释、家三家不断地争鸣、吸收、融合、创新,以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的鼎盛吗?还会出现像《六祖坛经》那样用完全中国化的语言与思维,简洁明了地切中释迦法旨的千古佳作吗?
是以学界的两种视角,只是因为切入角度的不同,而导致其观点相左。事实上,两个进程是同时的,相互交织的;正因为有了“中国”化“佛教”与“佛教”化“中国”的两个进程的同时发生与并进,才有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创新、融合,最后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第一次佛教中国化:再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出三藏记集•道安法师传》用“钩深致远”、“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来盛赞东晋道安大师在格义佛教背景下的锐意进取与开拓创新;而道安大师千古一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出佛教在中国弘扬最核心的原则与方针;道安大师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更是鲜明地呈现出道安对于当时佛教中国化最为前沿的解释与把握。道安大师可谓是中国佛教史上推进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基于道安法师传,我们可梳理出相关佛教中国化的三个原则:
佛教中国化的精神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佛教中国化的政治原则:必依中国,法事方立;
佛教中国化的方法原则:随机立缘,不拘不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道安大师之后,中国佛教一直在沿着道安大师所创立的原则不断地进行中国化。
(一)、佛教中国化的精神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佛教教义与实践之中国化进程回顾
佛教传入伊始,体系混乱,语系纷杂,经典缺乏。是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佛教的核心要义,难以有体系上的把握。于是产生了用中国本土固有之儒家、道家思想来阐释佛教义理之“格义佛教”:“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中国佛教史上的“格义佛教”,从道安始,就得到反思,经罗什,而致僧肇;僧肇以一部《肇论》,用完全中国化的语言、逻辑、思想背景,完成对于佛教核心要义“空”的精确阐释。
东晋以降,南北朝之始,中国佛教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原有的佛教核心教义之外,又增加了对实践佛教方法的关注。南北朝时期,随着传入经与论的量的累积,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出现了以研究某一部经或论为重心的“学派”现象,如“摄论学派”、“地论学派”、“涅槃学派”等等。而“学派”背后所呈现的意图有二:一、中国人试图以中国的语言、逻辑与文化为背景,更加系统地理解与把握各种佛教教义;二、中国人试图探索和把握精确的佛教实践方法论。
隋唐佛教则继承了南北朝佛教的二个核心意图,并最终完成中国宗派佛教的创立,并完成佛教教义与佛教实践的完全地中国化。一部《六祖坛经》,用最为质朴简练的中国语言、逻辑、文化背景,精确地阐释出印度佛教的核心要义与方法论,标示着印度佛教完美中国化的最高峰。
(二)、佛教中国化的政治原则:必依中国,法事方立的二层含义
道安大师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狭义地理解就是依国主,法事立。实际上,在道安大师之后,佛教依中国法事立,则呈现出二种走向:一、当依国主,则法事立;二、士僧互动,法事深入。
1、当依国主,则法事立
当依国主,则法事立,以南朝梁武帝护法为典型,在佛教史中处处呈现,此文不再赘述。
2、士僧互动,法事深入
士族阶层,为中国古代社会知识精英阶层,他们是中国政治与精神脊梁。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极盛背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是:士与僧的良好互动。东晋高僧道安与名士习凿齿之“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则成为士僧良好互动关系的生动写照与千古佳话。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很多僧人本身就出自士族名门。在道安之后,名士与高僧的机锋叠出,更多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深入地理解与把握佛教教义与方法,从而让佛教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终于筑就佛教在南北隋唐时期的繁荣昌盛。是以,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第一次成功的中国化,除了坚持“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原则外,士与僧的良好关系,成为中国古代佛教真正落地、生根、发芽、成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此点道安大师虽然没有言明,但从他与名士的交往,即可窥得一斑。
(三)、佛教中国化的方法原则:随机立缘,不拘不泥
道安遣法汰到扬州教化,嘱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遣法和入蜀教化,嘱曰:山水可以修闲。可见,教化之事当随机立缘,不可拘泥,而后方可移风易俗,这是佛教中国化方法论的原则。是以中国汉地佛教素食传统,自梁武以来蔚然成风,“学派”与宗派林立,禅宗之不立文字,当前棒喝,机锋连连,清规与戒律并行,都可谓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的方法论随机立缘,不拘不泥,遥契祖意,却又独具匠心。
(四)、小结:唐末以后中国佛教衰落原因管窥――保守与创新的张力与抉择
唐末以后,中国佛教经过北宋的整体维持、相对发展以后,自南宋开始,中国佛教便逐渐江河日下,及至晚清衰微尤甚。唐宋以降的中国佛教衰微之势,除其自身的原因之外,也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此处,笔者试图以大历史的视角,对于唐宋以后中国佛教衰落的原因进行管窥:
回顾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有二次国力与文化由衰向盛转变的时期。
第一次:春秋战国直至秦西汉时期。三代末期,中国由鼎盛走向衰微,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四分五裂,张力巨大。面对如此局面,儒、墨、道、法、兵、阴阳等诸子集中迸发,为家国天下,各呈已见,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此次,中国文化内在的自发性的迸发与创新,成就了以后秦汉一统天下,以及国力与文化由衰向盛的转变。
第二次:南北朝直到隋唐。东汉末期,中国文化与国力再一次触顶衰微,是以魏、蜀、吴三分天下,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最后还是进入东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南北分割,朝代迭更,战事频繁的乱世。此时,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为中国文化注入一股全新的活力,经过儒、佛、道的不断论争、融合与创新,最终成就了隋唐国力与文化的再一次鼎盛。
事实上,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入第三个由衰向盛转变的时期。北宋之后,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再一次触顶衰微,历经元、明、清,中国文化与国力多为保守,少有创新,及至晚清极度式微。晚清开始,中国有识之士已经放眼看世界,积极汲取西方文明,推动一系列的改革与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等,试图为中国文明再次注入新的活力。1911年辛亥革命用最为激烈的方式力图植入西方的文明模式。1945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运用各种方式,试图打破旧有的体制与束缚,快速推动中国社会再次走向鼎盛与繁荣,虽历经坎坷,但自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城乡模式、人际关系、价值序列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中国已经站在了全新的历史节点,为迎新下一个鼎盛的大中国与大文化的到来,作最终地努力与奋斗。
伴随中国国力与文化在唐末以后的触顶式微,实际上,中国佛教在唐宋以后的也逐渐衰微。佛教义学在充分中国化后,充分吸收佛教义学之后的宋明理学逐渐成为主流。此外,度碟制度的存废、佛教丛林宗法制度的盛行、太平天国运动的毁寺、晚清庙产兴学风潮等等,都促成中国佛教在晚清走向极度式微。
综上,笔者认为,唐宋之后的中国佛教的衰微,不仅仅是中国佛教个体的衰微,实际上,在唐宋之后中国国力与文化开始触顶式微。已经第一次完成中国化的佛教与中国已经是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伴随中国第三次由衰向盛的转变,中国佛教也必然将会迎来再一次由衰转盛的转变:第二次佛教中国化。
三、第二次佛教中国化的序幕
――人间佛教兴起的机与缘
晚清至民国,中国佛教已经沦落为死人的佛教,除了经忏佛事,佛教义学暗淡无光,佛教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大众的正能量也几乎为零。社会大众对于佛教僧团的评价已经从知识精英、文化精英、灵魂导师变为寄生虫!
迫于以上情境,1913年初太虚大师在上海佛教界为释寄禅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佛教革命三大主张’。所谓“佛教革命三大主张”,即是太虚大师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产的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他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卜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的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才,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
印顺法师是继太虚大师之后,在理论上积极推动佛教变革的又一人,他对人间佛教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阐释,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1941年,印顺在其专著《佛在人间》论述到:佛陀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何必执着?是的,不过我们现在人间,我们得认识人间的佛陀。佛陀是人间的,我们要远离拟想,理解佛在人间的确实性,确立起人间正见的佛陀观。佛是即人而成佛的,所以要远离俗见,要探索佛陀的佛格,而作面见佛陀的体验,也就是把握出世(不是天上)正见的佛陀观。这两者的融然无碍,是佛陀观的真相。在大乘佛教的发展中,如果说有依人乘而发趣的大乘,有依天乘而发趣的大乘,那么人间成佛与天上成佛,就是明显的分界线。佛陀怎样被升到天上,我们还得照样欢迎到人间。人间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间,就是天上,此外没有你模棱两可的余地。请熟诵佛陀的圣教,树立你正确的佛陀观: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也’!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人间佛教的迅猛发展,是以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特别是以“成为台湾佛教思想的基调”之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理论为指导的。
继太虚大师以后,如果说印顺法师主要在理论上指导了台湾人间佛教的迅速发展,那么赵朴初先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积极推动了以人间佛教为指导思想的大陆佛教的稳步发展。
赵朴初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明确提出了以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他在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指出:“在当今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赵朴初先生强调,须“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并把它作为中国各级佛协和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指导思想。他把大乘菩萨行作为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把修学菩萨行作为“修行佛道的中心课题”。赵朴初在人间佛教理论基础方面,与太虚大师、印顺法师相一致,都把建立在“五戒”、“十善”基础上的大乘菩萨行作为人间佛教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理论基础,但是他们人间佛教理论的具体内容因时代的变化而存有明显的差异。太虚大师强调人生佛教须与“三民主义”文化相适应,“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赵朴初依据新的时代要求,强调“佛教‘人间净土’的思想同社会主义不矛盾”,人间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因为“佛教的教义告诉我们要‘报国土恩,报众生恩’,要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他明确指出,中国佛教“从整体上和主流上看,它日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扩大开放的重要渠道。总之,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是党和政府可以信赖的同盟者,而不是异己力量。”因此,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不相违背”,“要求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继承先人的遗业,以人间佛教入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可以说,赵朴初的人间佛教,真正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把握了时代的根本精神,切合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为中国佛教的顺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没有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佛教事业的发达”。同时,中国佛教必须积极发挥“人间佛教入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朴老强调,以人间佛教理念为指导的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
由此,自晚清之后,中国佛教就已经自觉拉开中国佛教的第二次中国化序幕,积极融入中国第三个由衰向盛转变的际遇。
当前,中国佛教其实处于第二次佛教中国化最为关键的时期。中国佛教能否紧跟第三次中国文化与国力由衰向盛转变的节奏与机遇,成为当前中国佛教第二次中国化的最为紧迫的任务。
四、结语:第二次佛教中国化展望
(一)未来的中国展望:大文化的出现与大中国的崛起
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帝国,在世界史上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自晚清以来,跌入谷底,备受欺凌。中国有识之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则”之决心,一代又一代进行不懈地奋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就经济总量、国土面积等等而言,中国无疑早就恢复了世界大国的位置。但是,一个强国的延续,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这个心脏,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力量,即软实力。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世界文明史上最为关键的承上启下的节点:自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以科学技术为其核心支点的西方文明已经到达顶层,有如中国历史上的北宋。其后,西方文明必然会触顶下滑。目前西方文明在哲学界向东方文化寻求新的文化支点,就是一个昭示。而当前的中国已经为一种全新的大文化的产生做好的充分准备:旧有宗法制度已经被大幅削弱,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从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走向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传统的价值序列已经被冲破:目前的价值序列虽然有张力,但是多元,而且充满了开放性。中国政府与知识阶层充满了理性:未来中国的大文化,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完全复古,唯一的路径就是创新,但这种创新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其间必然经历迷茫、困惑、狐疑、阵痛,甚至倒退。但这一切又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大文化诞生前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而这种全新的大文化创新一旦完成这种,不仅会解决中国的问题,让中国真正地崛起,而且这种大文化的模式,会有如隋唐时期的文化一样昭示四海,延续千年。
此际,中国正处于世界文明史的最重要的节点,笔者展望:伴随西方文明的触顶,中国大文化的创新已开始全面发力。此际,西方文明虽然有向东方文明寻求新的发力点的倾向,但其主动性与意愿性并不强烈。而中国对于西方文明,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文明采取了饥渴样式地汲取;同时重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开始全面地、连续地试验与创新一种全新的中国大文化。是以,未来的世界,可能是全面创新的中国大文化的世界,这种整合了西方文明、东方文明,甚至世界范围内文明样式的大文化,会让中国的内心真正强大,并且延绵千年!彼际,大文化必然诞生,大中国必然崛起!
(二)未来佛教中国化展望:第二次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在中国历史上,印度佛教已经成功地完成第一次中国化,但是处于中国第三次由衰向盛转变期的中国佛教必然面临着全面的第二次佛教中国化。
事实上,道安法师第一次中国化的三个原则,在笔者看来,依然适用于第二次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由此,基于第一次佛教中国化的三原则,笔者认为中国佛教要完成第二次中国化应当基于三个要点:一、跟随中国现代化而完成现代化的改革。二、融入中国的大文化的创新,自觉得融入全新的中国体制、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从而积极完成中国佛教的第二次中国化。三、基于成功的、全面的第二次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必然跟随中国大文化的崛起而完成中国佛教的世界化。
无论何时,不可遗忘祖训;无论何时,都当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无论何时,都当坚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无论何时,都当随机立缘,不拘不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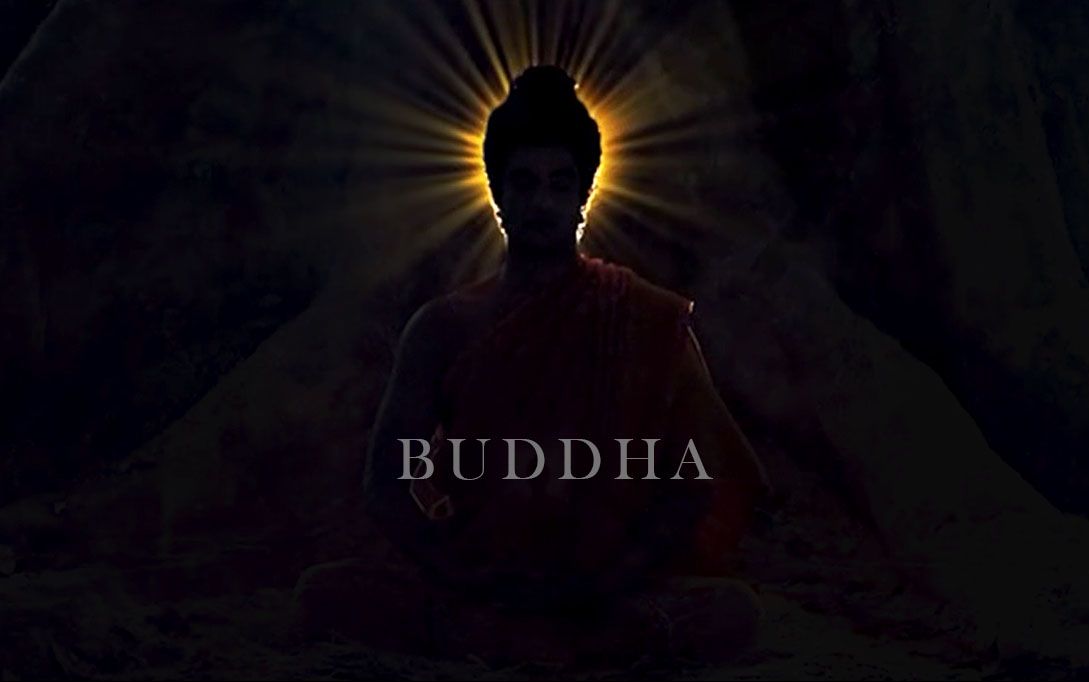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