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读常新的好文,真正读懂时,悟道不远矣
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
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
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坐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
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
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
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地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
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
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英国诗人(Blake)也说:
“一粒沙里见世界,
一朵花里见天国;
手掌里盛住无限,
一刹那便是永劫。”
节选自《缘缘堂随笔》丰子恺 著
(责任编辑:印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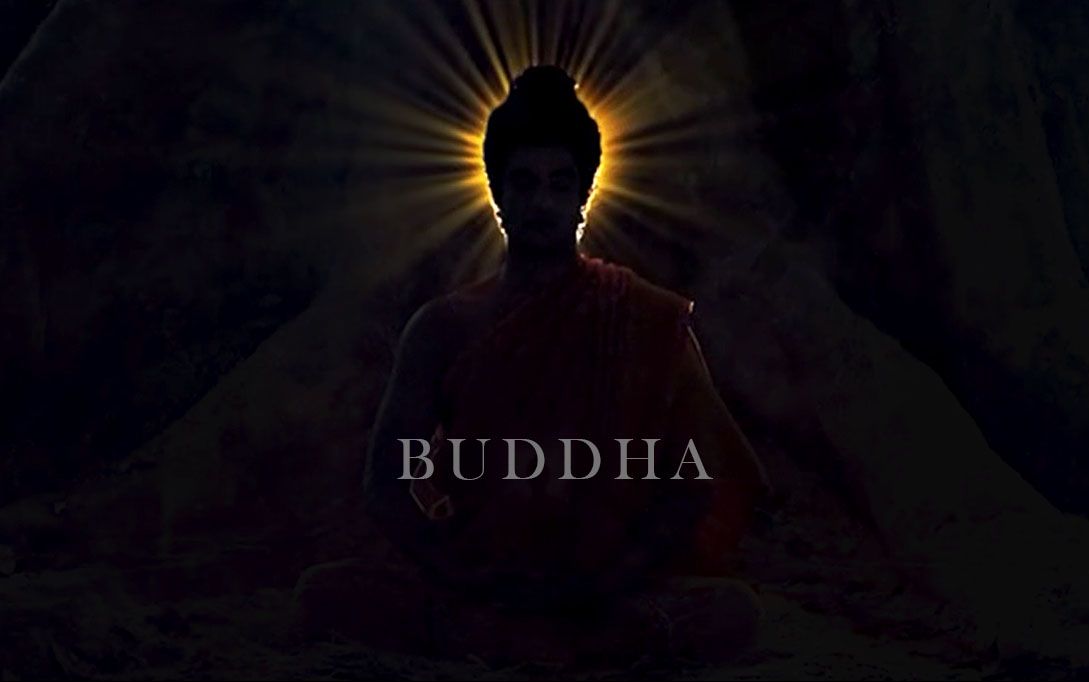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