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潜法师:天台宗祖庭国清寺早期行法初探
其实,杨广及隋王朝在此之前一直都有密切关注智者及其僧团的动向,早在隋灭陈后不久,即隋开皇十年(590)正月十六,隋文帝杨坚便下有敕书,对智者大师(时称光宅寺智顗禅师)及其所领僧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言辞很是严厉,文中强调“师既已离世网,修己化人”,故必须“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并警告说:“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抑恐妙法之门更来谤讟。宜相劝励,以同朕心。”智者大师示寂前,在新昌石城寺遗书与晋王杨广,文中云:“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据此亦可窥知隋朝政府当时对智者大师及其僧团的密切关注、诸多限制,且被地方官员冠以有乖国式、非法聚众、恼乱官人等罪名,僧众学子一千三百余人当天即被谴散。
有鉴于上述外部因素隋朝政府的具体要求,以及僧团自身内部实修的实际需要,智者大师在隋开皇十六年(596)春第二次入天台山时,看到晚学后进松散懈怠的不良情况:“观乎晚学,如新猿马,若不控锁,日甚月增”,为维护僧团的良好形象、成就僧众的无上道业,故立御众制法十条,以整肃僧团、训诸学者、明确赏罚、规定行法。其中第一条规定:“夫根性不同,或独行得道,或依众解脱。若依众者,当修三行:一、依堂坐禅,二、别场忏悔,三、知僧事。”
据此可知,智者大师在立制法十条当中,首先指出:根据各自的根性不同,有的可独自修行而得道果,有的则需依众共修而得解脱。若想依靠僧团大众之力而得解脱者,应当修行三种行法,即所谓:依堂坐禅、别场忏悔、知僧事。此是针对三种不同的僧众对象(依堂僧、别行僧、知事僧)而应机施设的三种相应的行法。也就是说,此三种行法,乃是智者大师所亲自制定的、当时天台僧团(后为国清僧团)所共同遵循修习的行法内容。若追溯此三种行法的思想渊源,或可从北凉时期所译的《大方广十轮经》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后世的文献中更进一步说明了三种行法乃是对应上中下三种根性而来的:上根性者坐禅,中根性者读诵(礼佛忏悔),下根性者营理僧事。
立制法中,智者大师针对三种不同的僧众对象,设有三种相应的行法:
1、依堂僧行法:“以四时坐禅、六时礼佛为恒务”,即所谓的“禅礼十时,一不可缺”。
2、别行僧行法:“别场忏悔”,即“以在众为缓,精进勤行四种三昧”;竟三日外,仍依众禅礼十时。
3、知事僧行法:知僧事,掌管、担任僧团诸事时,要求做到:不私果缕,不侵众物,不违本心,竭力供养;竭力始终供养读诵、听学、讲说、经行、忏悔者。并叙有三则规鉴:净人为奴前因、信照侵盐障道、众驴迎送私客。
据上可知,天台僧团(后为国清僧团)早期的行法最主要有四时坐禅、六时礼佛、四种三昧等,以下对此略作考察。
四时坐禅的行法来源,可在后汉安世高所译的《大比丘三千威仪》中找到理论依据,该书卷上有云:“欲坐禅复有五事:一者当随时……随时者,谓四时。”另据日本学者池田鲁参考察,从原始僧团日常日程的安排内容来看,四时坐禅早在释尊时代即有实行,乃是原始僧团日常修习的主要内容;但在智者大师以前的诸家文献著述中,未能找到“四时坐禅”作为一个词而出现,据此或可推知此行法乃是智者大师所最先提倡。南宋之际,日僧荣西(1141~1215)入宋求法,曾到天台山留学,回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在其所撰的《兴禅护国论》卷下中,记载了当时禅宗寺院日常行仪中僧众们不敢有所懈怠的行法亦是四时坐禅。其后不久,日僧道元(1200~1253),入宋求法,回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在其所撰《永平清规》中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四时坐禅,可知南宋时期智者大师当年示寂之地——越州(今浙江新昌)大佛寺一带,此行法亦颇为盛行。关于四时坐禅中的“四时”,其具体对应的时间,现代学者一般多解释为:黄昏、后夜、早晨、晡时。但此四个时间段,是否就是当时智者大师所说的“四时”,本人认为尚待进一步探讨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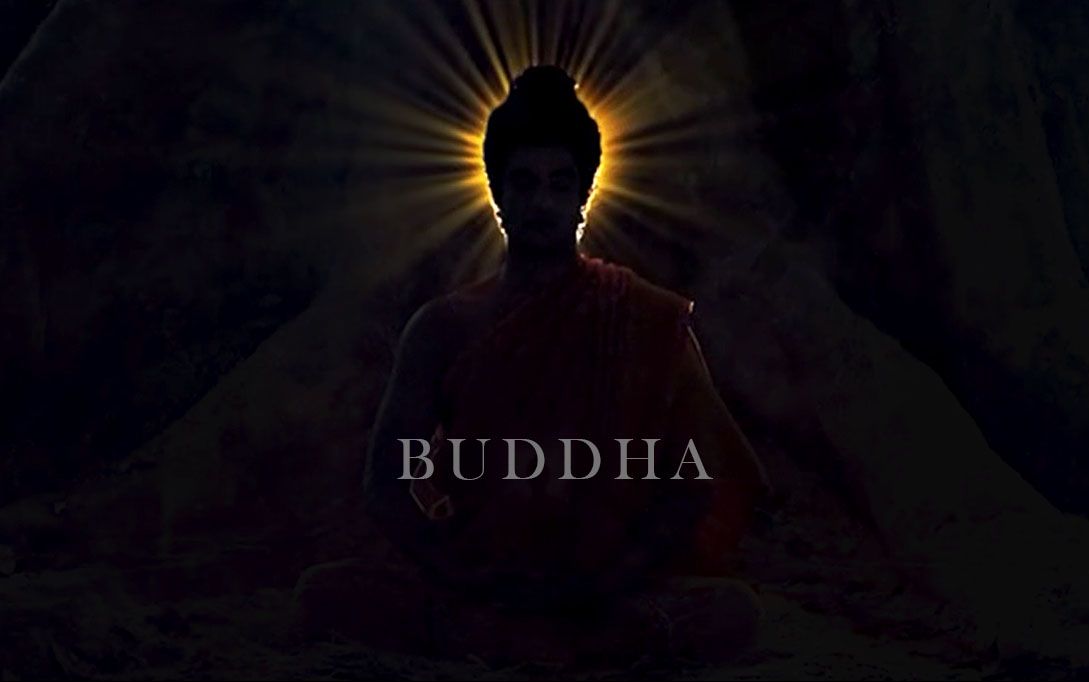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