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中:古代讲经与汉传佛教的辩经风尚

关于讲经法堂、法座,《续高僧传》卷五《僧旻传》有一记载很值得注意:
天监末年,下勅于庄严寺建八座法轮。讲者五僧,以年腊相次。旻最处后,众徒弥盛。庄严讲堂,宋世祖所立,栾栌增映,延袤遐远。至于是日,不容听众。执事启闻,有勅听停讲五日,悉移窓户,四出檐溜,又进给床五十张,犹为迫迮。桄桯摧折,日有十数。得人之盛,皆此类焉。旻因舍什物嚫施,拟立大堂,虑未周用,付库生长,传付后僧。[23] 此文中的“八座法轮”意思不大明了,也缺乏其他资料互证。推测言之,似乎是可以容纳八位法师同台参与讲经的“高座”。文中又说,建康庄严寺讲堂是刘宋世祖孝武皇帝刘骏(430年-464年,453年—464年在位)时期所建。这次讲经活动,五位高僧依次宣讲,僧旻因为僧腊最短而排在最后。然而听众却更多,甚至使讲堂人满为患,皇帝知晓后,下令停止五日,扩大讲堂,加座五十,仍然不足以容纳所有听众。僧旻“又于简静寺讲《十地经》,堂宇先有五间,虑有迫迮,又于堂前权起五间,合而为一。及至就讲,寺内悉满,斯感化之来,殆非意矣。”[24]这次也是人满为患,临时扩充讲堂。
二、“都讲”与“讲主”的互动
都讲是讲经法会中辅助主讲者,主要的任务是“问难”。从文献的记载推测,其身份、地位与主讲相比,略逊一筹。然而,“都讲”与“讲主”的互动使讲经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高僧传·僧导传》记载:僧导“形止方雅,举动无忤。僧叡见而奇之,问曰:‘君于佛法,且欲何愿?’导曰:‘且愿为法师作都讲。’叡曰:‘君方当为万人法主,岂肯对扬小师乎?’”[25]由此例中僧叡与僧导的对话可知,“法主”的地位更高。 如《续高僧传·灵裕传》卷二十记载:“时相州有灵智沙门,亦裕公弟子也。机务亮敏,著名当世,常为裕之都讲。辩唱明衷,允惬望情,加以明解经论,每升元席,文义弘远,妙思霜霏,难问锐指,擅步漳邺。”[26]依据此说,灵裕讲经时,弟子灵智常常充当“都讲”。 关于“都讲”的职责,《续高僧传》卷九记载说:“昔弥天释道安,每讲于定坐后,常使都讲等为含灵转经三契。”[27]此中的“都讲”承担的是“唱导”的职责。《续高僧传》卷二十八又记载:释善慧达到长安,“沙门吉藏正讲《法华》,深副本图,即依听受。形服鄙恶,众不纳之,乃扫雪藉地单裙[扌+亲]坐。都讲财唱,倾耳词句,拟定经文。藏既阐扬,勇心承旨,望通理义。”[28]此中似乎是说,都讲也承担“唱诵”经文的责任。 “都讲”的基本职责是“问难”。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兹举数例。 《高僧传》卷四《支道林传》记载:“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回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29]支道林是东晋时期最为著名的辩经僧,他不仅与高僧们互相论难,也与当时的玄学家论辩。这场宣讲《维摩诘经》的活动,道林担任主讲法师,许询担任都讲。二者相得益彰,论难和回应悬念迭出。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的最后一句,听众都称获得了支道林所讲的要旨,令其回忆自己叙说,不能完全说出所有论旨。 道宣在其《续高僧传》卷九《僧粲传》记录了僧粲与嘉祥吉藏配对宣经讲论法会的大致过程。其文说: 隋齐王杨暕,见礼下筵,钦兹叹咽。常欲见其谈说,故致于法会。有沙门吉藏者,神辩飞玄,望重当世。王每怀摧削,将倾折之。以大业五年于西京本第盛引论士三十余人,令藏登座,咸承群难。时众以为荣会也,皆参预焉。粲为论士,英华命章,标问义筵,听者谓藏无以酬及;牒难接解,谓粲无以嗣。往还抗叙,四十余翻,藏犹开析不滞,王止之,更令次座接难。义声才卷,粲又续前难,势更延累。问还得二三十翻,终于下座,莫不齐尔。时人异藏通赡,坐制勍敌;重粲继接他词,慧发锋挺。从午至夕,无何而退。王起执粲手,而谢曰:“名不虚称,见之今日矣。”躬奉麈尾什物,用显其辩功焉。而行摄专贞,不贪华望。[30] 此段文字记录的是齐王于大业五年(609)于其宅第组织的一次宣讲经论的法会,吉藏任讲主,僧粲任都讲。从道宣所录时人的赞语窥测,二者不分伯仲。也有学者将此记述解释为“辩论”,如汤用彤先生在论及吉藏时就说过:“曾与僧粲、智脱辩论,可见其纵横一时也。”[31]南北朝隋唐讲经,均有“讲主”和“都讲”之设,后者专门“问难”,由主讲回答。从场面上看,从今人的习惯言之,似乎有“辩论”性质,其实在当时是讲经的常规做法。另外,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提问。如果讲主不能回答“都讲”和其它人的问难,则自动下座。而吉藏与僧粲这一场讲经法会则是一场旗鼓相当、皆大欢喜的场景。 南朝的“瓦官寺”,乃是高僧萃集之所在。东晋初期,支道林曾经于其中宣讲《般若经》。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聴。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輙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此事应该发生于晋哀帝在位时期的兴宁二年或三年间(364—365),因为文中提及的竺法深是哀帝时期至京师建康的。 在讲经法会中,不但“都讲”可问难,所有听众都可以问难。也有僧人因此而脱颖而出,名声大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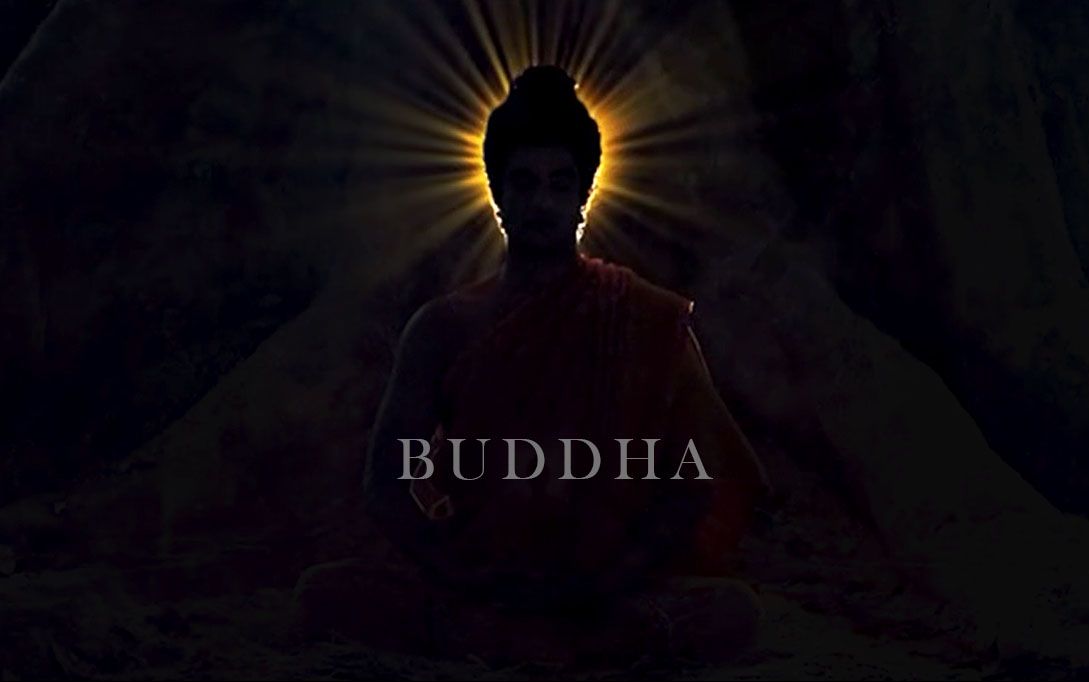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