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文法师:佛教戒律的法律性与道德性
摘要:佛教戒律既具有止恶的法律性,又蕴含着劝善的道德性,是法律性与道德性的统一。正是由于佛教戒律具有法律性,所以在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佛教戒律与国家的法律精神从根本上是统一的,并可以根据国家法制的要求,与时俱进,做出具有时代性特征的调整和完善。同时,也正是由于佛教戒律又兼具道德性,所以又要充分发挥其道德性的作用,对中国的法制与道德建设以及社会的稳定提供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佛教;戒律;法治;“五戒”
在佛教的戒、定、慧三学之中,戒律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因此,戒律是佛教之教法的根本内容。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作为外来文明,佛教只有充分地适应中国本土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并配合时代的演变,才能获得当地的政治上层和人民群众的接受和支持,其中戒律是佛教中国化程度最高的部分,因此,佛教戒律在中国历史法令和道德规范的影响之下,不断地调整与完整;而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的戒律逐渐深入人心,也从正面影响着民众的道德心理与行为,因而又成为国家法律制度的有益补充。
一佛教戒律与国家法律精神的统一
佛教虽然具有着鲜明的宗教性及其出世的精神,存在着胜义谛和世俗谛之分,但是佛教的戒律却是专门就世间法而立言的,其中既没有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智慧,也没有依于内在体证的不言之妙,而是明晰地规定了是与非、善与恶的差别与界限,此是犯,此是不犯,此应作,此不应作,分分明明。因此,佛教戒律在立法形式上与现实社会的法律精神是一致的。
从佛教戒律的产生来看,佛教戒律与中国自身的法律精神也是统一的。东西方文化虽然都有悠久的法制传统,但是在对待法律起源的问题上,东西方文化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而佛教戒律与中国的法制传统则保持着高度地一致性。通过对西方法制传统的考察可以看出,西方社会的法律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古罗马著名的法学家西塞罗说道:“我们需要的是解释法律的本质,而这个本质需要从人的本性中去寻找。”[1]P187在西方主流的文化传统中,人的本性往往被理解为邪恶,而非善良,这不仅体现在西方传统宗教的“原罪说”中,在思想界也被普遍地赞同,如近代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就主张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人性本恶,因此,人们应该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诚然,法律的基础一定是恶,只是因为有了恶,才会有法律制定并惩戒的必要,但是这个恶是否是基于人性本身,则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中西方文化认为法律的基础是人性的本有之恶,而东方文化则主张邪恶并非来自人性自身,而是环境造成了人性的邪恶。如中国最早提出“礼法”思想的荀子就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无所谓善与恶,只是在乱世之中,先天本性如果不加引导,就会趋向于邪恶,正如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也,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2]P934正是由于人性有不足,往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才有法律存在的必要;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人性先天又具有善良的一面,所以人类才能创制出道德与法律,来促人向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致,佛教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性善的本质,否则的话,人性又如何成就佛性呢?佛教认为,戒律之所以产生并加以运用,只是由于在娑婆国土这个五浊恶世之中,人性会趋向于邪恶,并遮蔽了佛性,所以,佛教根据人们行为上的过错,依据事实的案例,建立起各种防范的条文,通过戒律来加以止恶劝善。因此,佛教戒律不仅与中国法制传统保持着一致性,与现代法律制度也是相容的。
佛教戒律与国家法律的统一性,不仅体现在法律精神与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两者也是相互蕴含的。在历史上,佛教戒律就曾对国家法律的制定起到过借鉴的作用,如禅门清规自唐玄宗时的百丈禅师创制之后,影响深远,明太祖朱元璋所制的《祖训》以及清代康熙皇帝所颁布的《圣谕广训》,都是深受其启发。就佛教戒律的内容上来说,佛教戒律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加以划分,如根据戒律的对象,可以分为出家戒和在家戒,其中出家人的戒律又分为比丘戒和比丘尼戒;如根据戒律的性质,可以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和作持戒两种,其中止持戒是指禁止性的规范,作持戒是指应作为的规范;如果按照戒律的条目多少来划分的话,戒律又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比丘戒二百五十条和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等,而这些戒律从内容上来说,都体现了法律的性质。拿佛教戒律中最基础的“五戒”来说,“五戒”中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也都体现了法律的性质,起到了如法律一样的惩戒作用。
二佛教戒律的道德性是国家法律的有益补充
佛教戒律不仅具有法律的属性,能够起到止恶和惩戒的作用;而且包括着对纯真、至善行为的倡导,蕴含着道德的属性,具有劝善的功效。例如佛教中著名的“七佛通偈”,具体内容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其中的“诸恶莫作”是指戒律的止恶,“众善奉行”是指戒律的扬善。从中可以看出,佛教戒律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范畴,对人们提出了比法律更高的道德要求。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很多,如法律是对人们行为的基础性规范,而道德则是对人们行为的高尚性要求;法律是事后惩罚,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中具有消极性,而道德则往往是事前干预,能够防患于未然,具有积极性;法律规范具有外在性、他律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而道德则具有内在性、自律性和自愿性的特点等等。正是由于道德具有法律所不具备的诸多特点,所以道德才能够成为法律的有益补充。在今天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固然要坚持法治的主导,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应该积极地发挥道德对法律的有益补充作用,正是在这一方面,佛教戒律在当代中国,将会有重要的作用。
佛教戒律不仅具有法律的特征,还同时具有道德的诸多特点。佛教戒律之所以具有道德性,这是由佛教自身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决定的。佛教以解除无明烦恼为目标,以追求涅槃寂静与成就佛果为根本理想,而这些目标和理想的实现,都离不开戒律的有效实行,正如《四十二章经》曰:“佛子离吾数千里,忆念吾戒,必证道果,在吾左右,虽常见吾,不顺吾戒,终不得道。”[3]73南山律师道宣也说:“戒律难思,冠超众象,为五乘之轨导,实三宝之舟航,依教建修定慧之功莫等。”《华严经》更是直言:“戒是无上菩提本。”所以佛教戒律必须要超越法律的基础要求,而进行更加高尚的道德性规定,正如台湾佛教学者劳政武说道:“佛教戒律之主要目的,一在使教团的秩序及发展得以维持及确保,二在使徒众能得精神解脱证取佛果,故极重道德性诚属必然。”[4]P159
以“五戒”为例,“五戒”不仅对应着五种惩戒条目,中国律宗还常常将“五戒“对应于十种善业,也就是说,中国佛教不仅仅从止持的消极方面来理解戒律,而且还从积极的方面来运用戒律。十善业道分别指放生、布施、梵行、诚实语、和诤语、爱软语、质直语、不净观、慈悲观和因缘观。在“五戒”与“十善”的对应之中,不杀生对应着放生,以不伤害生灵为底线,并倡导积极地救生、护生;不偷盗对应着布施,以不偷盗为基本的要求,并在主动地奉献中培养慈悲之心;不邪淫对应着梵行,以不邪淫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并通过清净自体来圆满一切智德;不妄语对应着诚实语、和诤语、爱软语和质直语,以不欺骗为待人待己的基本界限,并在更高层次上要求诚信待人和在语言上与人为善;不饮酒对应着不净观、慈悲观和因缘观,通过对酒的禁止,发挥理智的主导,实现精神的专一,以此来实现道德的目标。
在“五戒”之中,不饮酒不仅是佛教戒律与其它宗教戒律的重要区别,而且也最能体现佛教戒律的道德性特征。酒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本身是无善无恶的,但是佛教将不饮酒作为一项极其重要且基础的戒律之一,正是考虑到道德的理性保障。道德虽然是源自于人的情感,但又要通过人的理性去控制和规范情感,因此,情感是道德的基础,而理性却是道德的保障。一个人在饮酒之后,理性的力量就会被酒精所削弱,人的感官与情感往往就会摆脱理性的缰绳而放纵,如此一来,“五戒”之中的其他四戒的防线就会容易被攻破,而做出违背道德,甚至法律的事情来。
佛教戒律的道德性还体现在“五戒”与“五常”的相配。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佛教逐渐与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相融合,并进行相互诠释,其中“五戒”与“五常”的佛、儒互释就是重要的表现之一。如《摩诃止观》曰:“不杀生配仁,不偷盗配义,不邪淫配礼,不饮酒配智,不妄语配信。”[5]P77“五常”是儒家最重要的五个道德原则,分别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爱的意思,仁爱又存在三个递进的层次,其一是亲亲之爱,其二是他人之爱,其三是万物之爱,因此,佛教将儒家之“仁”与不杀生相配。“义”是正义的意思,往往与利相对,是指在公义与私利面前的抉择,所以“义”与不偷盗相配。“礼”是行为规范的总和,是管控人的官能的主要力量,如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6]P123所以“礼”与不淫邪相配。“智”是指是非之心,尤其是指一个人的理性原则,所以与不饮酒相配。“信”是指不巧言令色,诚实守信,故以不妄语相配。儒家“五常”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五种道德原则,而与佛教之“五戒”一一对应,从中就明确表达了佛教戒律的道德属性与作用。
三佛教戒律的当代性诠释及其积极意义
佛教作为世界古老的宗教之一,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发挥着积极的影响,以及能够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生正面的作用,就在于佛教自身具有着开放性与变革性的特点,具有着与时俱进的重要品质。拿佛教戒律来说也同样如此,早在佛陀在世之时,佛陀就曾对戒律在将来的发展与变革进行了肯定,如他说道:“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静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7]意思是说,即使是我所制定的戒律,如果不能达到心性的寂静,都可以废止;即使不是我所制定的戒律,如果在当下需要加以运用,也可以增加。正是在佛陀的指导之下,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不断地改变自身形态,接受并消化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与政治制度,如吸收四维八德,接受拜神宗,尊敬王者和孝敬父母等;与此同时,佛教戒律也在不断地中国化,如唐代律宗的产生,以及禅宗清规的发明等,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佛教戒律,皆非囿于原始佛教的戒律的范围,而是有了新的创造与发展,正是这种创新,才使得佛教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了普遍的传播与发展。
站在当代中国的视域之中,佛教戒律也应该结合时代的特征,进行新的诠释,以能够切实地发挥其当代的价值与作用。仍然拿佛教的“五戒”为例,“五戒”中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所欠缺和珍贵的。
第一,不杀生。不杀生是指不伤害一切生灵,不仅包括人,而且还包括动物、植物等一切有情之物,“一切有形、蠢动、含灵,皆不得加害”,这个思想在当代社会就具有了生态意义,对维持自然的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佛教主张不杀生,也由此而引申为戒堕胎,这对形成健康的男女关系,培养优良的社会道德风尚,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不偷盗。戒盗在今天经济社会中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在当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商品的诱惑以及欲望的膨胀,使得金钱至上的观念流行于世,这就促使一些人唯利是图,以非法的手段获取不义之财,如贪污、走私、偷税漏税、卖淫等等,因此,佛教要求不偷盗,使人安其本份,不贪图小利,对和谐社会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不邪淫。除了夫妇之间的男女关系之外,一切不受国家法律或社会道德所承认的男女关系,均可称为邪淫,《四十二章经》曰:“爱欲莫甚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3]P52,现代中国法律的要求是一夫一妻制,如果人人都能够遵循法律的要求,安于一夫一妻的家庭生活,就不会有各种奸杀、情杀、强奸、诱奸、卖淫、嫖娼等恶劣现象的存在,也会大大地降低离婚率,以及由离婚所造成的单亲家庭等社会问题,由此可见,不邪淫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四,不妄语。妄语即虚妄不实的言语,不妄语就是指言语诚信。诚信是中国传统一直所倡导的道德原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今天,妄语的现象到处存在,如在网络上散播谣言属于妄语,夸大的商业广告属于妄语,各种吸引人们眼球的“标题党”是妄语,各色各样的花边新闻也是妄语,由此可见,妄语的当代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五,不饮酒。饮酒本身虽然无关乎法律与道德,但是饮酒之后,人们就可能丧失理智,并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许多触犯法律与违背道德的行为都与饮酒有关,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酒驾与醉驾,因此,在全社会上下倡导不饮酒,或者少饮酒,将有助于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佛教所制定的戒律,从立戒的本意上说,主要是为了起到防非止恶的作用。但所制定的戒律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佛教对待戒律还可以有“开、遮、持、犯”这四个方面的变通和应用。凡是面对着善的、正义的、对社会国家众生有利的方面,即使是杀戒,也是可以有开缘的。比如抗日战争年代,我国也有很多爱国佛教徒站出来组织队伍英勇抗日杀敌。但对于不能开戒的地方,一定要严持不犯,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和神圣。佛陀在临涅槃前对弟子们嘱咐说:“我涅槃后,汝等当以波罗提木叉为师”。即使是佛不在了,只要弟子们能坚持“以戒为师”,才能使佛教保持永久的纯洁性和延续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也是一样,无论是时代的更迭还是政府的换届,只要有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和延续,那么国家和社会就会有安定局面的保障。
综上所述,佛教戒律具有法律性与道德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佛教界应该积极地依照法制的要求,革新并加强佛教的戒律,与国家依法治国的大原则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佛教界还应该积极发挥戒律的道德属性,积极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引领信教群众朝向更加美好、高尚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贡献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1]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M].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2]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尚荣译注.四十二章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4]劳政武.佛教戒律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5]大正藏,卷46。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7]大正藏,卷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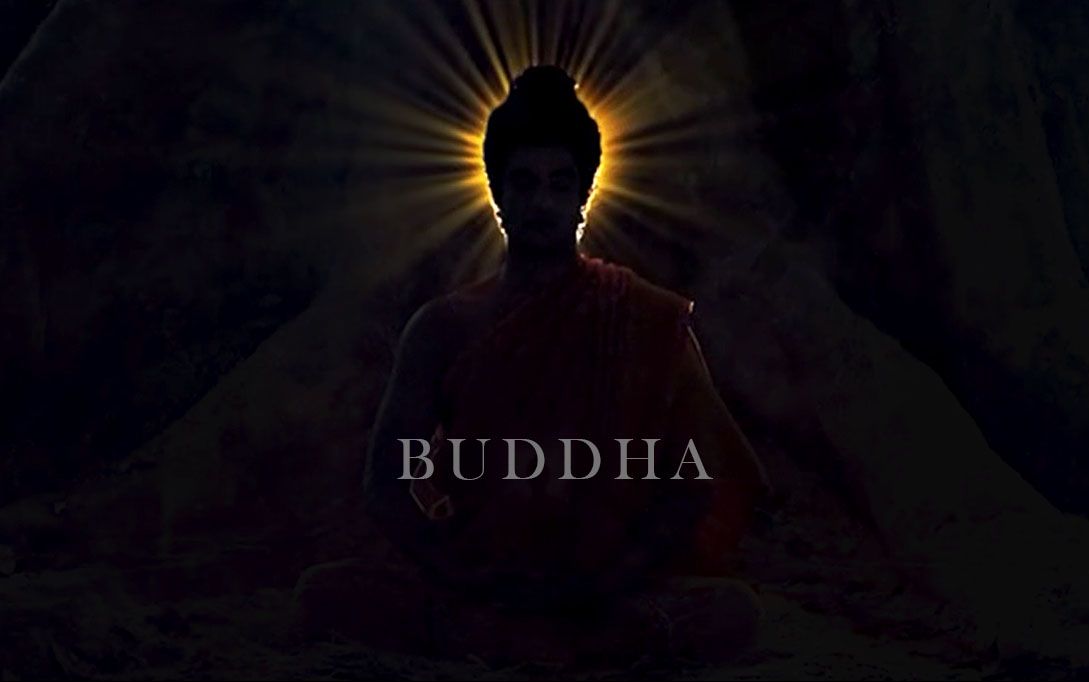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