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美:智顗与《菩萨戒义疏》关系考辨
菩萨戒在汉传佛教戒律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汉传佛教菩萨戒有《瑜伽》系和《梵网经》系两个系统。其中《梵网经》菩萨戒是主流,是后世三坛大戒中菩萨戒的主要依据。隋唐以后形成的各个宗派大都重视《梵网经》,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等都有不少有关《梵网经》菩萨戒的注疏,可以说对《梵网经》菩萨戒的重视是超越宗派界限的。其中,天台宗对《梵网经》菩萨戒地位的确立影响最大,而天台宗的实际创造者智顗正是开启这一历程的重要人物。本文就是通过辨析智顗与《菩萨戒义疏》(以下简称《义疏》)的关系,展现智顗对《梵网经》菩萨戒在汉传佛教中流行的贡献。
《义疏》是现存最早的对《梵网经》菩萨戒的注疏,也是在汉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菩萨戒注疏。佛教界历来认为《义疏》为智顗所作。20世纪中期,日本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代表性人物主要有佐藤哲英,他在《天台大师の研究》一书中指出《义疏》不是智顗的著作,但在8世纪初已经存在。他否定《义疏》为智顗所作的理由主要有:(一)早期文献资料如灌顶的《智者大师别传》、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大唐内典录》中未有记载。(二)天台三大部对《梵网经》之引用甚少。(三)天台所述“持戒清净”中与《梵网经》无关系。(四)《义疏》主张色法戒体,与智顗在其他著作中的观点不一致。(五)书中使用三重玄义,而非智顗常用的五重玄义。对此台湾学者陈英善曾进行了反驳。本文综合两家观点,通过考察其他史料中对《义疏》的记载、《义疏》出现的背景、智顗对《梵网经》的重视、《义疏》与智顗其他著作的关系等,认为《义疏》主体部分是智顗所作,但也加入了后来天台弟子(或者即是灌顶)的思想。
一
天台九祖湛然(711—782)门人明旷所著《天台菩萨戒疏》提到:“今随所欲,直笔销文,取舍有凭,不违先见,则以天台为宗骨,用天宫之具缘,补阙销释,贵在扶文,则诸家参取。”陈英善认为:“天台为宗骨”应是指智顗的《义疏》及天台教义。另外,陈英善还从《义疏》所论及的六种菩萨戒本来分析,认为:“此中所述的六种戒本,时间大约集中在南北朝时期,由此时间似乎可推知《义疏》成立年代约在梁隋之际。”
笔者赞同陈先生的看法,再补充几点证据,《宋高僧传》卷第十七《唐越州焦山大历寺神邕传》云:
(邕)又从左溪玄朗师习《天台止观》、《禅门》、《法华玄疏》、《梵网经》等四教三观等义。
左溪玄朗为天台宗八祖,《止观》《禅门》《法华玄疏》都是智顗的著作,将《梵网经》与前三书列在一起,并称为“……等义”,正说明智顗对《梵网经》有注疏之作。
早期文献资料没有著录《义疏》,可以这样解释。《智者大师别传》完成于智顗去世后九年,即公元606年,此时属于天台三大部的《法华文句》、《摩诃止观》都没有最终完成,在《别传》中都没有著录,《义疏》可能也是因为没有编撰完成,才没被著录。《续高僧传》(645年完成)、《大唐内典录》(664年完成)没有著录《义疏》可能与唐初期天台宗的实际状况有关。在智顗的大力弘扬和陈、隋帝王的极力支持下,天台教义在陈、隋两代曾非常兴盛。智顗去世后,纲领天台山的智越(543—616)在义学上似乎没有多少建树,但因为智顗与晋王杨广的关系,智越主持天台期间,仍得到皇室的大力支持,整个僧团保持了较大活力。后来被认为继承智顗法统正宗,并被天台宗尊为五祖的是追随智顗十几年,记录整理智顗大部分著作的灌顶(561—632)。智顗去世后,灌顶在天台僧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智顗去世后第二年(598),灌顶曾亲赍“石城遗书”赴扬州,呈于晋王杨广,杨广很快便按照智顗的遗愿建立国清寺。此后灌顶与杨广保持了很好的个人关系,大业七年(611),已登帝位的杨广领兵打仗期间,仍派人到灌顶行所,“叙以同学之欢”。总之,天台宗在整个隋代都保持了很大的影响。但也许正是由于天台宗与杨广的这种密切关系,加上隋末的大乱,后继者缺少弘化之才,入唐后天台宗一度消沉。智越去世后,其弟子中并没有杰出者。灌顶则“纵怀丘壑,绝迹世累,定慧两修,语默双化”,并于贞观六年入寂。此后,继承灌顶法脉的六祖智威、七祖慧威、八祖玄朗,在义学上都没有太大建树,生平事迹也少闻于世,天台宗在一段时间内与唐前期兴起的华严、法相、禅宗等相比黯然失色,直到唐中期九祖湛然(711—782)重新注疏天台三大部,才使天台宗出现中兴的局面。湛然门人梁肃曾用“明道若昧”来描述天台宗这段暗淡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灌顶在智顗过世后整理出来的一些智顗著作不被唐前期的一些文献记载,就不足为怪了。
《义疏》在唐初资料中没被著录,但在新罗却似乎很受重视。新罗僧人元晓(617—686)所著《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中有几处似乎与《义疏》有关,如:“(杀法)《疏》云,以杀具刀杖等为法。然而无合于义。”考察《私记》所涉及的内容,此处的《疏》应该就是指《义疏》。《私记》中有:“今此卷者,《梵网经》大部中一品,上卷者明菩萨心地法门,此下卷中明菩萨戒相。”与《义疏》相关论述基本相同。另外,杀戒中约三品众生辨非、六种杀的分类以及构成重罪的条件等内容与《义疏》也非常相似。元晓生活的时代基本在唐前期,公元644年曾与义湘一起计划入唐求法,但未成行。元晓对《梵网经》非常重视,据《韩国佛书解题辞典》所载,他关于《梵网经》的著述有五种:(1)、《梵网经宗要》,一卷,失。(2)、《梵网经疏》,二卷,失。(3)、《梵网经略疏》,一卷,失。(4)、《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二卷,上卷存。(5)、《菩萨戒本持犯要记》,一卷,存。《私记》作为对《梵网经》的一种注疏,虽在文字上与《义疏》没有太多直接关系,但应该参考了《义疏》的内容。此后,新罗华严宗创立者义湘(625—702)门下十大德之一的义寂作《菩萨戒本疏》,《本疏》在文字上多处直接使用了《义疏》的内容。可见当时,《义疏》在新罗已经非常流行。而与义湘同学于智俨门下,比义湘小18岁,被奉为华严宗三祖的法藏(643—712)所著《梵网经菩萨戒本疏》中却几乎看不到《义疏》的影响,《本疏》中有言:
又闻西国诸小乘寺,以宾头卢为上座。诸大乘寺以文殊师利为上座,令众同持菩萨戒,羯磨说戒,皆作菩萨法事,律藏常诵不绝。然声闻五律四部,东传此土,流行其来久矣。其于菩萨律藏逈不东流,昙无谶言于斯已验。致使古来诸德或有发心受戒,于持犯暗尔无所闻。悲叹良深,不能已已。藏虽有微心,冀兹胜行,每慨其斥阙,志愿西求,既不果遂,情莫能已。后备寻藏经,捃摭遗躅,集菩萨毗尼藏二十卷,遂见有菩萨戒本,自古诸贤未广解释。今敢竭愚诚,聊为述赞,庶同业者粗识持犯耳。
法藏羡慕西国大乘寺菩萨戒的普遍传诵,感慨汉地菩萨律藏的缺失,想西行寻求,但没有如愿以偿,于是遍寻藏经,从中集出20卷菩萨毗尼藏,并发现了菩萨戒本,即《梵网经》菩萨戒本。对这一戒本,自古以来没有人进行过详细的解释。据此,法藏生活的时代,不仅《义疏》,就连《梵网经》菩萨戒也流传不广。但既然新罗僧人能够看到,足以证明其在8世纪以前就存在。新罗佛教与中国天台宗关系密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谓:“南岳慧思有弟子玄光,受《法华安乐行门》,证法华三昧,后归国行化。而高丽释波若,亦曾入天台山受智者教。……宋初天台典籍散失,而高丽谛观乃返送其国所存者来华也。”也许《义疏》在隋代即由僧人带至新罗,并因是智顗著作而广泛流行,在汉地却因隋末大乱而少有流传,后来由新罗僧人传回汉地得以广泛传播。
二
翻阅智顗著作,我们发现其对《梵网经》引用次数确实不多,但对《梵网经》评价却非常高。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二:
第二广明持犯者,从初心至佛果,以明持犯有十种:……七持智所赞戒。发菩提心,为令一切众生,得涅槃故持戒。如是持戒,则为智所赞叹。亦可言持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此戒能至佛果故,为智所赞叹。……后四是出世间上上戒净。若能如上所说受持。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简称《次第禅门》),为智顗在金陵弘法时(569—575)讲述,由弟子法慎记成三十卷。后来,经过灌顶删定编辑,制定为十卷。这是智顗较早的著作,在《智者大师别传》中著录。其中,将《梵网经》十重四十八轻戒规定为十戒中的第七戒智所赞戒,属于出世间上上戒,“能至佛果”,可见对其重视。
《法界次第初门》卷上:
次此应明在家优婆塞、优婆夷,一日一夜八戒,出家沙弥、沙弥尼十戒,式叉摩那尼六法戒,比丘、比丘尼十种得戒,五篇七聚相,乃至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及三千威仪,八万律仪。
《法界次第初门》是智顗在天台隐修期间(575—584)所作。其中列了各种戒的名称,按其排列的顺序,似乎把菩萨十重四十八轻作为高于具足戒的戒法。
《妙法莲华经文句•释寿量品》:
《梵网经》结成华严教,华台为本,华叶为末。别为一缘,作如此说,而本末不得相离。
《法华文句》在《智者大师别传》中没有著录,但据潘桂明《智顗评传》,陈祯明元年(587)智顗在光宅寺讲授《法华经》,弟子灌顶后将讲经内容整理成《法华文句》。此处认为《梵网经》属于华严教,这在智顗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中属于第一时、别教、顿教,是仅次于《法华经》、《涅槃经》的经典。
《法华玄义》卷三:
他云,《梵网》是菩萨戒。今问:是何等菩萨戒?彼若答言:是藏、通等菩萨戒者,应别有菩萨众。众既不别,戒何得异?又若别明菩萨戒,何等别是缘觉戒?今明三藏三乘无别众,不得别有菩萨缘觉之戒也。若作别、圆菩萨解者,可然。何者?三乘共众外别有菩萨故别有戒。
《法华玄义》是灌顶根据智顗在玉泉寺讲说的内容(593)整理而成的,属于智顗后期成熟的思想。此处,智顗认为《梵网经》菩萨戒属于别教、圆教菩萨戒,圆教是智顗化法四教中最高、最究竟的教法。与在《法华文句》中的地位相比,《梵网经》菩萨戒在此处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
《摩诃止观》卷四:
次观因缘生心即中者,观于心性毕竟寂灭,心本非空,亦复非假。非假故非世间,非空故非出世间,非贤圣法,非凡夫法。二边寂静,名为心性。能如是观,名为上定。心在此定,即首楞严。本寂不动,双照二谛,现诸威仪,随如是定,无不具足。如是观心,防止二边无明诸恶,善顺中道一实之理,防边论止,顺边论观,此名即中而持两戒也。故《梵网》云:戒名大乘,名第一义光,非青、黄、赤、白。戒名为孝,孝名为顺。孝即止善,顺即行善。如此戒者,本师所诵,我亦如是诵。当知中道妙观,戒之正体,上品清净究竟持戒。
《摩诃止观》也是智顗在玉泉寺所讲,智顗生前及《智者大师别传》中称为《圆顿止观》,后来又经过灌顶整理,改名为《摩诃止观》,代表天台宗的成熟思想。在智顗的三观(空观、假观、中观)体系中,中观具有最高最终极的意义,此处将《梵网》戒与中观结合在一起,认为《梵网》戒具备止、行二善,“中道妙观”是“戒之正体”,从而确认了《梵网》戒在戒律中的最高位置。
综上所述,智顗在其著作(除《义疏》外)中虽然没有过多提到《梵网经》,但《梵网经》菩萨戒在其思想体系,尤其是对戒律的认识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而且随着其思想体系的渐趋成熟,《梵网经》菩萨戒的位置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智顗著作(除《义疏》外)关于戒律的部分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地持经》菩萨戒,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反证。
三
智顗对《梵网经》的重视不仅体现在理论上,更体现在实践上。在菩萨戒的授受中,智顗应该是以《梵网经》菩萨戒为主要依据的。据《国清百录》《智者大师别传》等记载,陈代有不少大臣、王子、后妃跟随智顗受菩萨戒,如陈金紫光禄王固、侍中孔焕、尚书毛喜、仆射周弘正等,“俱服戒香,同飡法味”。陈永阳王,“眷属同禀净戒”。陈后主,“太子已下并托舟航,咸宗戒范”。《别传》里虽然没有直接说明这些人受的是何种戒,但据《国清百录》中的请戒文,可以知道应该都是菩萨戒。至于是何种菩萨戒,《国清百录》里没有明确交代。《国清百录》中有一篇隋炀帝作晋王时请智顗授菩萨戒的疏文,其中有:“谨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管金城设千僧蔬饭,敬屈禅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显然是引用了《梵网经》的内容。智顗去世后,兼秘书监柳顾言奉隋炀帝之旨撰写了《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其中这样描述杨广受戒的情况:
(晋王杨广)以为能仁种觉,降兹忍土。信相入道,净戒居先。《梵网》明文深传萨埵,国师僧宝必兼禅慧。……于时天地交泰,日月载华,庭转和风,空净休气。林明七觉之华,池皦八净之水。化覃内外,事等阿输之城。教转法轮,理符宝冥之窟。文武寮寀,俱荫慈云,欣欣焉,济济焉,肃肃焉,痈痈焉。经所谓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显发三愿,真正十受。……睿情犹疑未满,以为师氏礼极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吕望之称尚父。检《地持经》智者师目,谨依金口,虔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顶礼。
杨广认为修学佛道“净戒居先”,并引《梵网经》来证明受菩萨戒的重要性。接下来文中提到所受戒的名称为“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这种名称显然来自于《地持经》。受戒的内容为“显发三愿,真正十受”,“显发三愿”应该是指归依三宝,“真正十受”应该是指《梵网经》十重戒。三归十戒的受戒次序正是《梵网经》试图确立的戒学新规范。而将授戒师称为智者,则是《地持经》的说法。可见智顗为杨广所授菩萨戒当以《梵网经》为主要依据,并结合了《地持经》的内容。智顗为其他人所授菩萨戒也应如此。既然智顗如此重视《梵网经》,那么为其作疏,使之更容易被理解、被接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
如果我们比对《义疏》与智顗其他重要著作《法华玄义》、《四教义》等文字,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一致性。《义疏》对于菩萨阶位的描述和《法华玄义》《四教义》中的论述基本是一致的,尤其与《法华玄义》相对照,不仅菩萨阶位几乎相同,文句更是基本一致,只不过《义疏》的文字更为简略、明晰,有时甚至因为过于简略而容易引起理解上的偏失,有时也因为消减了一些文字而变得意义不明确。如在论述圆教十信位的最后,有这样一句:“是名圆教铁轮十信位,圆教似解六根清净也。”这里后半句很难理解,如果参考《法华玄义》就会明白,《义疏》省略了一些词句,完整的表述应为“是名圆教铁轮十信位,即是六根清净,圆教似解暖顶忍世第一法。”这样意思就很清楚,这是在比配声闻的阶位。
《义疏》很可能像智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是由智顗讲说,弟子们(可能是灌顶)修订完成,其主体思想是智顗的,弟子们又将智顗其他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概括加入,并系统化,也难免会有弟子们的看法。另外,《义疏》在列别教菩萨阶位后,有一段文字,讨论了性种姓、习种姓的关系以及解行位的四种名称。这段文字不见于《法华玄义》和《四教义》,倒是在净影慧远的《大乘义章》中有类似论述。慧远与智顗基本生活在同一个时期,智顗直接引用慧远著作的可能性也有,但更大的可能是智顗的弟子们将慧远的论述加入其中。
总之,笔者认为,无论从《义疏》出现的时间,智顗对《梵网经》的重视,还是其中所体现的天台宗思想,都可以将《义疏》看作智顗的著作,但也不排除其中掺入了其他人的思想。无论如何,智顗对《梵网经》的重视,为确立《梵网经》菩萨戒在天台宗乃至汉传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夏德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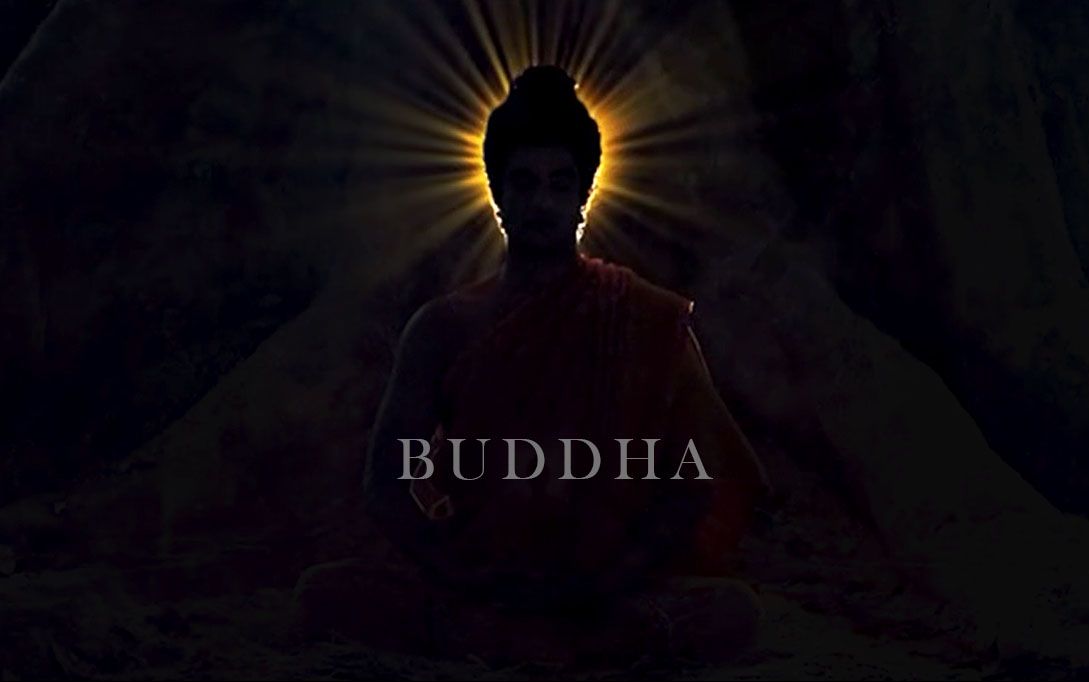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