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伟:天台“圆教”与隋唐帝国“意识形态”
【内容提要】“圆教”不惟是一单一的宗派理论之表说,更是隋唐宗派佛学对佛教新型“样态”的一种构拟,故具有一“职能”履行性。作为“圆教”形式的最早表述者,天台智者大师之贡献正在于,面对新的帝国时代之到来,其自觉从理论上将作为“出世间法”的“佛教”表述、扩展为“圆教”,使之成为超出传统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上的普遍“礼法”,以此承担帝国之广义“意识形态”的职能。
【关键词】天台圆教 隋唐帝国 普遍礼法 意识形态
前言
作为第一个中国化佛学宗派,天台宗以“教观双美”著称,其雄浑博大的思想体系向为世人所景仰、称赞。不过在慨叹智者大师超逸群伦之智的同时,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台宗于陈隋之际自命“圆教”,峻拔独立而睥睨他教,此“意味”着什么?自然,作为一理论表说,“圆教”乃确立于智者大师之手,故我们可以说天台“圆教”乃是天台宗对自身殊胜地位的合法性说明;不过考虑到陈隋之际社会政治形态的巨大转折,则我们以为,“圆教”不惟是一单一的宗派理论之表说,更是智者大师对佛教新型“样态”的一种构拟。换言之,“圆教”具有一“职能”履行性。天台智者大师的贡献正在于,面对新的帝国时代之到来,其自觉从理论上将作为“出世间法”的“佛教”表述、扩展为“圆教”,使之成为超出传统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上的普遍“礼法”,以此承担帝国之广义“意识形态”的职能。
一“宗派”佛学与“帝国”意识形态
相对于六朝的分裂格局,隋唐王朝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统一帝国时期。与帝国雄浑气质相匹配的是,虽然儒家学说在隋唐相对仍处低潮,而佛道二教则发展出宏大的宗派理论体系,为种族与文化多元性、疆域之辽阔性的帝国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特别是佛教高步雄视,相继演化出天台、华严等几大宗派,将汉语佛教哲学推向了一个高峰,成为隋唐帝国意识形态的主体。其中,作为最早成立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理论尤具有原创之功。
“宗派”乃是一个思想形态学的概念,其尤指这样一个学说组织,即其不但具有明确的学说宗旨身份且有一严格之谱系传承作为保证。隋唐佛教宗派有别于此前的六朝论派佛学,对此汤用彤先生曾有说明,其以为从广义上讲,六朝、隋唐佛学均可称“宗”,然二者区别在于,前者是就“义理”而言,而后者则就“人众”来说。自然,由“义理”之宗到“人众”之宗并不意味着隋唐佛教宗派不谈义理,相反隋唐宗派佛学正是中国佛学义理的高峰期,因此这个“人众”只是突出强调隋唐宗派佛学的组织特色。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要对宗派佛学形态作一更确切有效的说明,还是必须考虑到六朝与隋唐社会政治组织形态上的差异。可以说,隋唐佛学之所以是“宗派”佛学,乃是因为其不再是地域性的学说思想,而是在全局范围内成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自然,我们说宗派佛学为隋唐帝国的意识形态,此乃是在“广义”或“中性”而言,而非狭义上的作为统治秩序合法化工具的“意识形态”,因为尽管隋唐乃是三教鼎立特别是唐代道教还有相当之势力,然总体上是佛学担纲,为帝国之维持与运作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指导与精神凝聚力的保证,故宗派佛学之意识形态地位乃是“制度”性或可说是“中性”的。自然,如此而说并不意味着在现实操作层面,佛教会“自明”地获得此一合法地位,相反,陈隋之际的佛教有一“末法”危机意识,面对新的社会政治格局的逐渐形成,佛教同时面临机遇挑战。因为随着隋帝国的建立,时代政治对佛教思想界提出了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帝国的成立,六朝南北政治地理的割据局面得以结束,此统一之格局要求有相应之整合性思想体系的给出,故需要对南北朝区域性的差异学派佛学进行调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隋唐帝国面临着对差异之种族、文化因素予以整合的问题,即如陈寅恪所指出,种族与文化问题实为唐史之关键。对此韩昇、林悟殊等当代学者作了进一步演绎发挥,说明了在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下隋唐帝国处理种族与文化差异问题的重要性。故此,隋唐帝国的建立乃是一制度文明的创新,藉此将极为多元的种族、文化因素纳入到同一政治文化共同体中,而佛学在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缘由于此,我们看到,隋唐宗派佛学乃是得到了帝国“制度”性地支持,这一支持不单纯是出于政治人物的统治策略之方便,譬如隋皇室之高度重视天台宗确有稳定南方、争取人心的考虑,更是帝国本身内在结构性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宗派佛学与中央政治有一特别之关系,即宗派之兴衰往往与政权更迭相伴随,其典型便是隋炀帝之与天台宗、唐太宗之与唯识宗、武周政权之与华严宗。对此,学界已有相当深入之研究,如陈寅恪特别分析了唐武则天如何借助佛教为其执政寻求理论上的合法性,而此种倚重亦有实际的寻求胡人政治力量支持的考量。
隋唐宗派佛学既为隋唐帝国之精神总纲,故其学说体系建设表现出相当大的创造性,此主要体现在:以台贤为代表的隋唐宗派佛学在理论构建上博大而涵容,能够将种种差异的思想因素予以调停整合,将之纳入到一个据于自身立场的更大的思想形式中。为此,相对于六朝学派佛学,隋唐宗派佛学均有一自觉的树立己派“宗旨”的意识,并在理论上将之合法化,此特别表现为通过判教形式来确立本宗的“圆教”地位。从形式上看,隋唐佛学之判教乃是依循佛教经典为佛之方便说法之事实,对东传汉地之佛典全体予以高下权实之判释,以确立最终究竟之说的经典所在;而实质上,判教乃是不同宗派依据自身的思想立场,藉对既有佛教之诠释来安立本宗学说的最高地位。故相对于六朝佛学之“照着”说,隋唐宗派佛学不是围绕“梵胡经典”翻译展开文本疏义,而是依托某部经典而申发义旨,确立其新说,故乃是“接着”说。由于隋唐宗派佛学成立于不同“判教”体系的建立,故宗派论辩亦主要围绕“判教”体系展开。因为不同宗派尤其是台贤二宗,其“判教”之给出意在确立各自的“圆教”地位。“圆教”意味着最圆融的“教法”,故有其至高的尊贵性、权威性,但“圆教”其实不是从“佛说”之脉络给出,并非是对“佛”之言教史“事实”的认定,而实是中国佛教思想家一当下性的思考,是对“佛教”所作的“思想形态”构拟。换言之,“圆教”并非只是所谓佛教的某一特别或最高阶段性之教法,而乃是隋唐佛教大师给出的“唯一”有效的、合法的佛教新形态;从形式上看,“圆教”乃是佛教内部“协议”的结果,只是要解决佛教自身教法差异性的问题,而实质则是佛教学者为应对新的帝国政治形式,藉对传统佛教形态的“反思”、“批判”、“整合”,解决佛教存在的合法性危机,进而转型、扩展为一普遍的意识形态。因此,佛教判教之目的在于对佛教自身作一反思性处理,以便以一新形态的形式定位佛教,确立其职能所在,而“圆教”实际只是此佛教新形态的代名词而已。至于为何要以“圆教”之名来表说之,原因在于,“圆”既意指圆融、圆通,则“圆教”即谓“圆融至极”之“教”,以至于,其不惟是局限于“佛教”内部范围的“佛说”之“言教”,而是在更广大范围内的调停世间法/出世间法之“教”。由此,佛教才能以一普遍学说的身份,“充任”帝国意识形态的职能。天台宗之“圆教”之设意在此也。
二世间法/出世间法的调停:一切不出“法性”
如上所述,智者大师既给出一“普遍性”之“圆教”,则此“圆教”虽仍隶属于“佛教”,然已超出了佛教原有之身份范围,从而获得了一更大之职能。具体来说,原有佛教之身份乃是所谓“出世间法”,而有别作为“世间法”的儒家“礼法”;至于作为“圆教”的“新佛教”,则不自限于一“出世间法”身份,而是由“出世间法”扩展为一更为普遍的“礼法”,从而在更高层面上调停了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对立。从理论上讲,“圆教”取得此一身份职能之依据在于,一切法“不出”法性,均以“实相”为“体”(礼)。
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一般来说,从佛教之角度讲,“世间法”是指维护基于“我执”之世俗生活形式的制度规范乃至价值观念,出世间法则反之。早期佛教虽然出自“沙门“思潮,然其最终扭转“沙门”外道“禁欲苦修”之修证方式,而示以“八正道”之“中道”之行,开启“智慧解脱”之门。故佛教虽然自命为出世间法,只是“弃舍”世间生活的“染污”成分,而非全盘否定“世间”生活。因此,当代“人间佛教”的提倡者印顺法师再三强调,佛陀修行、证悟、教化均在“人间”;而现代“菩萨乘”论的提出者吕澂居士亦特别区别了佛教之声闻乘/菩萨乘,指出佛教“出世”修行之根本在于“转化”染著世间,所谓“即世而转世”。凡此这些申明乃是要说明,佛教虽有“出世间法”之名,并非是“消极”避世,而有其“转化”世间的积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虽名“出世间法”,而并不完全与“世间法”对立,其可在更高层面上承担“世间法”之职能。所以从狭义上讲,“佛教”之“出世间法”乃是对立于“世间法”,是否定作为维护“我执”生活形式的制度规范,然从广义上看,“佛教”之“出世间法”隐含了一更高层面之“世间法”意涵。
自然,一般所云之“世间法”只是“泛指”,并没有一特别明确之所指,而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世间法”即等同于儒家名教“礼法”,成为一“定指”。将世间法/出世间法对置为儒家礼法/佛教之关系,这是东晋佛学大师庐山慧远特别的思想贡献。在其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中,针对世俗人士的质疑,慧远提出了世间法/出世间法分别,申诉了释子豁免行世俗礼法之理由。所谓“法”,其实就是广义之“礼法”,世间法也就是指规范世俗之人的礼法,至于出世间法则是修行清净解脱者的礼法。慧远承认世俗之人(包括在家居士)必须恪守世间礼法,原因在于,世俗之人乃是顺化之民,故求“厚身存身”,既处“自然”状态,则父母双亲之恩爱、君王人主之资养不可忘,未可“受其德而遣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故要求忠孝敬拜。至于出世间法,乃是作为方外之宾的职守原则,而不同于世俗之人所守之礼教。因为出家人乃是“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非是顺化之人,故不贵厚生,不重运通。释子身份既不同世俗之人,其职守但在于息患达道,故其不得同礼世典。虽然出家者不服世法,然其必须守“出世间法”,所以慧远并没有否定职守/礼教之对应关系,恰恰要根据不同层次严格地恪守礼法原则。同时,故较诸魏晋名士的不拘礼教,作为方外之人的慧远倒是确立了世俗之人与世间礼教的对应关系,重新恢复了名教的合法性。如是,通过出家而求解脱,慧远在更高层面调停了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矛盾,从而开拓了士人生命更大的可能性。
显然,庐山慧远对世间法/出世间法关系的说明指示了,虽然出世间法高于世间法之层次,然二者各有权限,不可淆乱;即便前者能够“迂回”地“裨助教化”,间接地履行“世间法”之职能,然二者之畔域界限是分明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六朝时期虽三教论衡,互有攻伐,然各教甘于自身之特殊性身份职能,并不希冀有一更高层次的身份职能追求。这种情况到了隋唐帝国时代,即发生转变。如前所述,帝国政治之维持需要一普遍之意识形态学说之支持,故宗派佛学的兴起乃是契合此一时代,不过佛教既然要承担一普遍意识形态之职能,则其就不能甘居特殊性的“出世间法”之身份,而必须扩大其身份职能。为此,宗派佛学之给出“判教”,乃是藉“判释”“佛”之“言说”的形式,重新整理、组织佛教,从而确立一“新”的佛教形态,“圆教”正是此一佛教新形态的表现。不过,“圆教”既然是要承担一普遍性之意识形态职能,则所谓“圆教”就不惟局限是在佛教内部而言,实应理解为是在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上的一个“教法”。正如宋明理学(新儒学)乃是儒家吸纳佛道因素,将既往之儒家“礼学”扩展为普遍性的“理学”一样,隋唐宗派佛学之“圆教”则是佛教吸收儒学(包括道家)因素,将“出世间法”的佛教扩展为一“圆融”性的“佛教”,亦可云是一“普遍”性的“礼法”。那么“佛教”作为这一普遍性之“礼法”,其理据何在呢?对此,智者大师提出了一切存有之法不出“法性”(实相),当依“实相”为“体”(礼)的思想,从而给出了最有理论价值的说明。
“诸法实相”概念乃出于《法华经》,本指众生果报境界之种种方面的表现,所谓“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由于“佛”之知见“广大深远”,能了知、究竟此种种境界,故其得以应众生之“性欲”,开示种种“善巧”方便。虽然“佛”之知见非众生所能知,然“佛”之开示《法华经》的目的正在于令众生“了知”、“悟入”“佛”之知见。可见,在《法华》经典文本中,“诸法实相”乃是基于佛/生之“言教”关系,特指众生“果报境界”之表现,以相应说明“佛”之化他能力,而并无理体原则之抽象义。即至《法华玄义》,智者大师乃将“诸法实相”抽象化为一“理体”(法性)概念,用以解说“存有”之“法”的“体性”。故在以“五重玄义”之“辨体”解释《法华经》“经体”时,智者大师说道,“体字训礼,礼,法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君臣撙节。若无礼者,则非法也。出世法体亦复如是,善恶凡圣菩萨佛,一切不出法性,正指实相以为正体也”。在此,智者大师将“体”视为“礼”,即一套礼法规范,其借世间法说明,世间行为需要以儒家纲常名教之“礼”规范、节制之,同样,出世间行为亦需要相应之“礼法”规范,此一“礼法”即是“法性”(实相)。事实上,智者大师不惟以“法性”为出世间行为之“礼法”,且是世间、出世间一切“存有”之“法”的“礼法”,所谓“一切不出法性”。“法性”既为“一切法”之“礼”(体),则既往所谓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差异、对立也就由一“外在”性,转变为一“内在”性。换言之,判别世间法/出世间法的最终根据不在“行人”之“身份”,而在“行人”对“法性”之了达程度。故如其云,“故《寿量品》云:不如三界见于三界,非如非异。若三界人见三界为异,二乘人见三界为如,菩萨人见三界亦如亦异,佛见三界非如非异,双照如异。今取佛所见为实相正体也”。显然,同见“三界”之法,由于“行人”对“法性”的了达程度有异,故有不同之知见境界。进言之,行人“见”的层次与“见”相应“法性”的程度是一致的,“见”愈受“法性”之“规范”,则也就愈照见“法性”。以“法性”(实相)为存有之法的“法体”,其实也就是要揭示“诸法”的空假中三谛“结构性”,不过隔历三谛尚为“粗法”,非“究竟”实相,圆融三谛方为“妙法”、“究竟”实相。故从这个视角看,藏通别圆四教之次第给出乃是相对于“三界之人”的“世间法”,“但空”、“不但空”指藏、通二教,“但中”、“不但中”则为“别教‘、“圆教”,此一层级推进正说明,“圆教”之“礼”(礼法)乃为本经“正体”,行人当依此“体”(礼法)而修。
确立“圆教”之“礼”(礼法)为本经之“正体”,而以圆融三谛方为诸法之“结构性”所在,如此,行人“修行”之“场域”即无有限制,而可即就“一切法”,所谓“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就将“佛教”之职能范围由特殊性之“出世间法”领域,扩展至一般之“世间法”领域。如此,从佛教“自行”与“化他”之关系来说,就不是机械地以“自行”为“实”,“化他”为“权”,而是表现为一可“诠释”性。即如智者大师所云,“既不会正体摄属何法,但空是化他之实,但不但是自行化他之实,出二边中是自行之权,并他经所说,非今体也。今经体者,体化他之权实即是自行之权实,如垢衣内身实是长者;体自行化他之权实即是自行之权实,如衣内系珠即无价宝也;自行之权即自行之实,如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况自行之实而非实耶”。《法华》经本以“佛”之“知见”为“自行”之“实”,以种种善巧方便为“化他”之“权”,“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就是要藉“权”而入“实”,故自行/化他尚有实/权之对立。而经智者大师之诠释,自行/化他关系转为“自行”对“法性”的不同通达状态。这样,作为“佛”之“化他”手段的“治生产业”可以充任“众生”之“自行”,所谓“自行之权即自行之实,如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
这样一种表述,其实也就将佛/生并置于同一场域空间,由此二者之别不再是“听说”角色之异,但在于对“治生产业”之“结构性”的通达程度而已。换言之,“佛”可以而且必须“介入”到“一切世间治生产业”中。因为众生虽“处于”“一切世间治生产业”中,然其不“自觉”,未能了达诸法之“体”。故此“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之命题,其之表述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说明了世间之人可藉“世间行为”而通达“实相”,此是对传统佛教承担“出世间法”职能“特权”的一种“放弃”;而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对这种“特权”“放弃”,佛教反而扩大了其“权能”,得以更普遍的“礼法”身份参与到世俗社会中。就此,我们或许可以在一更高的思想层面上把握智者大师与时为晋王的杨广之互动关系,杨广尊智者大师为师,极尽弟子之礼,而智者则为其授菩萨戒,二者之间虽存有一紧张博弈关系,不可否认正是通过此一博弈,天台宗得以获得中央王权的支持,从而在隋代有一特别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天台“圆教”之建设实是佛教应对新兴帝国政治格局之表现。在对传统佛教予以重新系统化的组织、诠释的基础上,天台宗将佛教由一特殊性之“出世间法”发展为一普遍之“礼法”,从而承担其帝国意识形态之角色,为隋唐制度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原标题:天台“圆教”与帝国“意识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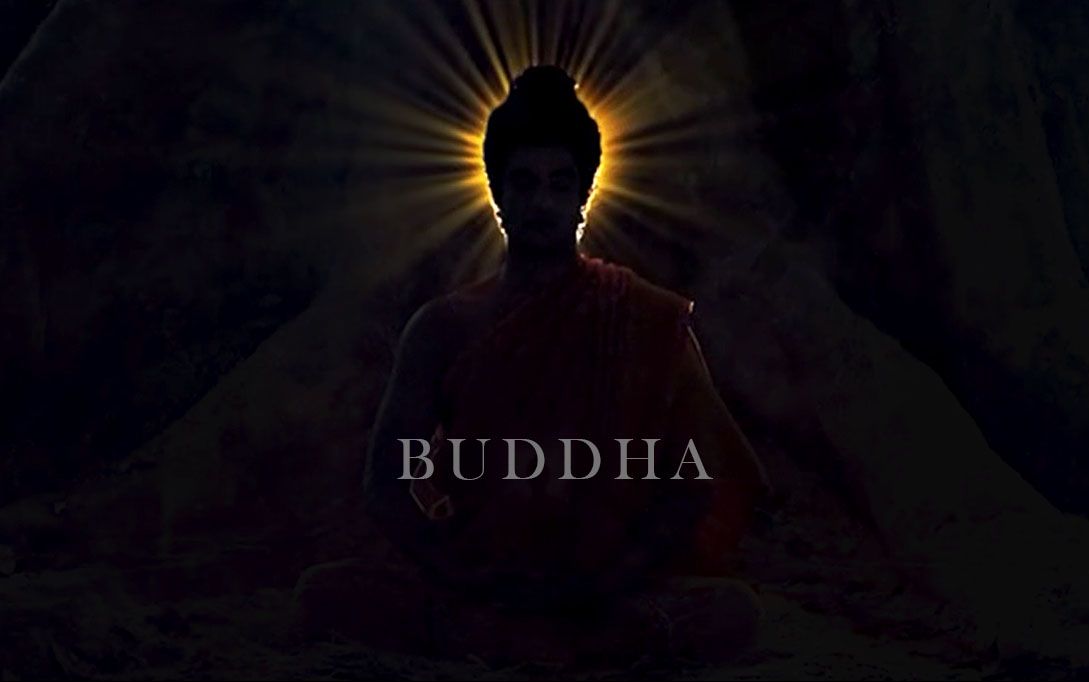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