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如法师:再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第二次佛教中国化略论
一、中国化的两种视角
在学界,有关佛教中国化的问题,最少有两种视角:一是“中国”化“佛教”,二是“佛教”化“中国”。
(一)“中国”化“佛教”——以道安为例
佛教的传入,必须适应中国本有的文化土壤、社会制度、风俗人情,特别是得到当时政权的认可,唯有这样佛教才有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以东晋道安大师指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可以说是推动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道安提出的这一原则核心是“依靠国家政权立佛法”即向佛教界提出了如何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种适应,要求佛教主动适应社会,接受国家政权的管理。也就是说,在佛教的管理体制上,他正在考虑中国化的管理方式。所以,“依国主,立佛法”的原则,实际上强化了佛教的社会性和政府性。佛教的社会性和政府性的特征,就是主张佛教的活动要与政权建设相协调。佛教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众,以此争取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支持。从而建立国家的权利与佛教大众的权利的互动关系。道安“依国主,立佛法”的主张,把中国儒家的“君臣”纲常关系融进了印度佛教。
此外,道安在理论上创立学派,兴起中国式般若学;在组织上建立了以道安为核心的释姓汉僧网络;在制度建设上探索了中国佛教的管理新路;在信仰上创立了一种适应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新模式。道安从各方面进行的改革,全面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
(二)“佛教”化“中国”——依牟宗三观点
就文化价值而言,如果佛教完全被中国同化,则佛教就已经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就佛教自身而言,无论如何变通外在的形式,而作为佛教最核心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是不能改变的,否则佛教如何被独立识别?是以自两汉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僧人不断东来,其核心目的,无非是为了传播佛法:即将佛教的核心方法论与价值观传到中国。是以牟宗三先生认为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其义理变化具有一致性,而所谓中国化的东西,都是表面迹象的不同。佛教“虽处在中国社会中,因而有所谓中国化,然而从义理上说,他们仍然是纯粹的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生命与智慧之方向对于他们并无多大的影响,他们亦并不契解,他们亦不想会通,亦不取而判释其同异,他们只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尔为尔,我为我。因而我可说,严格讲,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只是中国人讲纯粹的佛教,直称经论义理而发展,发展至圆满之境界。”“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都是一个佛家,它的不同……是表面那些迹象不同。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表面迹象的不同……就说有一个中国的佛教又有一个印度的佛教,好像有两个佛教似的,这是不对的。只有一个佛教。”既然所谓的中国化只是表面迹象的不同,因此从整体而言,中国佛教仍然是对印度佛教的一脉相承,佛教未曾中国化。
(三)小结:在互化中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与繁荣
事实上,在学界之所以有以上二种观点,也只是因为视角的不同:就“中国”化“佛教”来讲,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传播到中国,必然要适应中国的政权制度、社会结构和价值序列,以此视角分析,佛教必须要中国化,否则佛教何以在中国立足?是以东晋高僧道安高举“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积极全力推动佛教的中国化。而第二个视角是就佛教本身传播佛法的核心价值与目的来讲,无论佛教如何在中国,或主动中国化,或被动中国化,对于佛教僧团来说,其得以维系几千年延绵不绝的秘诀在于:佛教核心方法论与价值论的代代传递,这就是法身,这就是慧命。以此视角则佛教从来没有被中国化,而是将其核心的方法论与价值观传到中国,斯谓“佛教”化“中国”。我们可以假想:如果佛教传来到中国之后,被先秦诸子如儒、道、法、墨、兵法、阴阳等任何一家完整或彻底地同化,即其核心方法论置换为或儒、或道、或法等任何一家,那么佛教还有单独存在的意义吗?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还会有儒、释、家三家不断地争鸣、吸收、融合、创新,以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的鼎盛吗?还会出现像《六祖坛经》那样用完全中国化的语言与思维,简洁明了地切中释迦法旨的千古佳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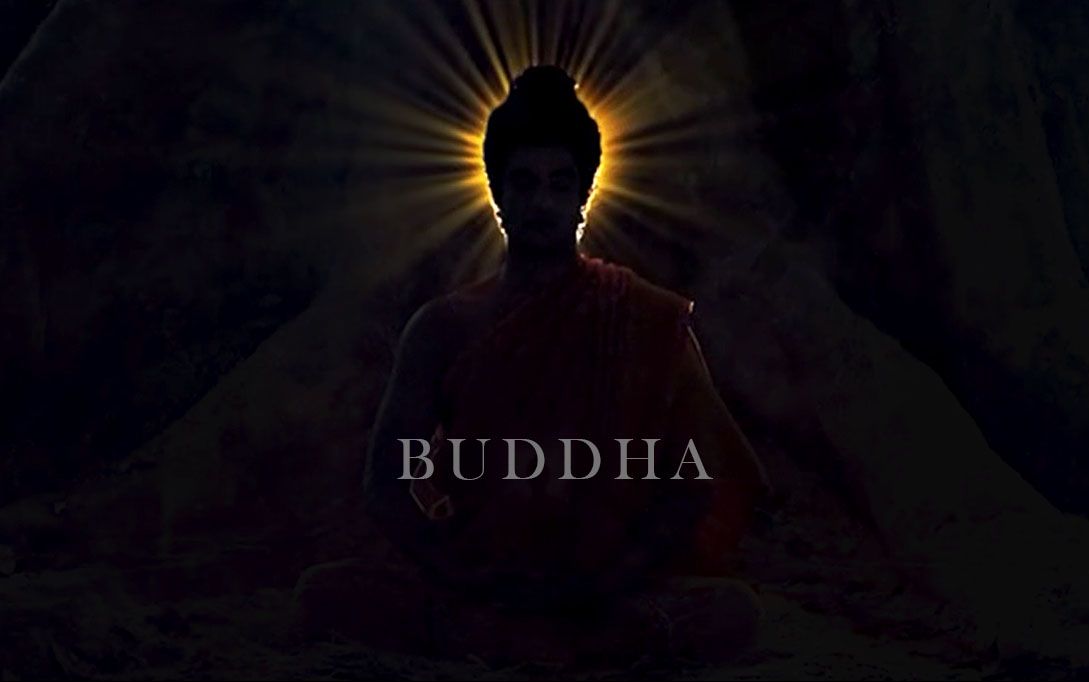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