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如法师:再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第二次佛教中国化略论
是以学界的两种视角,只是因为切入角度的不同,而导致其观点相左。事实上,两个进程是同时的,相互交织的;正因为有了“中国”化“佛教”与“佛教”化“中国”的两个进程的同时发生与并进,才有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创新、融合,最后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第一次佛教中国化:再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出三藏记集•道安法师传》用“钩深致远”、“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来盛赞东晋道安大师在格义佛教背景下的锐意进取与开拓创新;而道安大师千古一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出佛教在中国弘扬最核心的原则与方针;道安大师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更是鲜明地呈现出道安对于当时佛教中国化最为前沿的解释与把握。道安大师可谓是中国佛教史上推进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基于道安法师传,我们可梳理出相关佛教中国化的三个原则:
佛教中国化的精神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佛教中国化的政治原则:必依中国,法事方立;
佛教中国化的方法原则:随机立缘,不拘不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道安大师之后,中国佛教一直在沿着道安大师所创立的原则不断地进行中国化。
(一)、佛教中国化的精神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佛教教义与实践之中国化进程回顾
佛教传入伊始,体系混乱,语系纷杂,经典缺乏。是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佛教的核心要义,难以有体系上的把握。于是产生了用中国本土固有之儒家、道家思想来阐释佛教义理之“格义佛教”:“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中国佛教史上的“格义佛教”,从道安始,就得到反思,经罗什,而致僧肇;僧肇以一部《肇论》,用完全中国化的语言、逻辑、思想背景,完成对于佛教核心要义“空”的精确阐释。
东晋以降,南北朝之始,中国佛教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原有的佛教核心教义之外,又增加了对实践佛教方法的关注。南北朝时期,随着传入经与论的量的累积,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出现了以研究某一部经或论为重心的“学派”现象,如“摄论学派”、“地论学派”、“涅槃学派”等等。而“学派”背后所呈现的意图有二:一、中国人试图以中国的语言、逻辑与文化为背景,更加系统地理解与把握各种佛教教义;二、中国人试图探索和把握精确的佛教实践方法论。
隋唐佛教则继承了南北朝佛教的二个核心意图,并最终完成中国宗派佛教的创立,并完成佛教教义与佛教实践的完全地中国化。一部《六祖坛经》,用最为质朴简练的中国语言、逻辑、文化背景,精确地阐释出印度佛教的核心要义与方法论,标示着印度佛教完美中国化的最高峰。
(二)、佛教中国化的政治原则:必依中国,法事方立的二层含义
道安大师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狭义地理解就是依国主,法事立。实际上,在道安大师之后,佛教依中国法事立,则呈现出二种走向:一、当依国主,则法事立;二、士僧互动,法事深入。
1、当依国主,则法事立
当依国主,则法事立,以南朝梁武帝护法为典型,在佛教史中处处呈现,此文不再赘述。
2、士僧互动,法事深入
士族阶层,为中国古代社会知识精英阶层,他们是中国政治与精神脊梁。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极盛背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是:士与僧的良好互动。东晋高僧道安与名士习凿齿之“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则成为士僧良好互动关系的生动写照与千古佳话。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很多僧人本身就出自士族名门。在道安之后,名士与高僧的机锋叠出,更多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深入地理解与把握佛教教义与方法,从而让佛教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终于筑就佛教在南北隋唐时期的繁荣昌盛。是以,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第一次成功的中国化,除了坚持“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原则外,士与僧的良好关系,成为中国古代佛教真正落地、生根、发芽、成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此点道安大师虽然没有言明,但从他与名士的交往,即可窥得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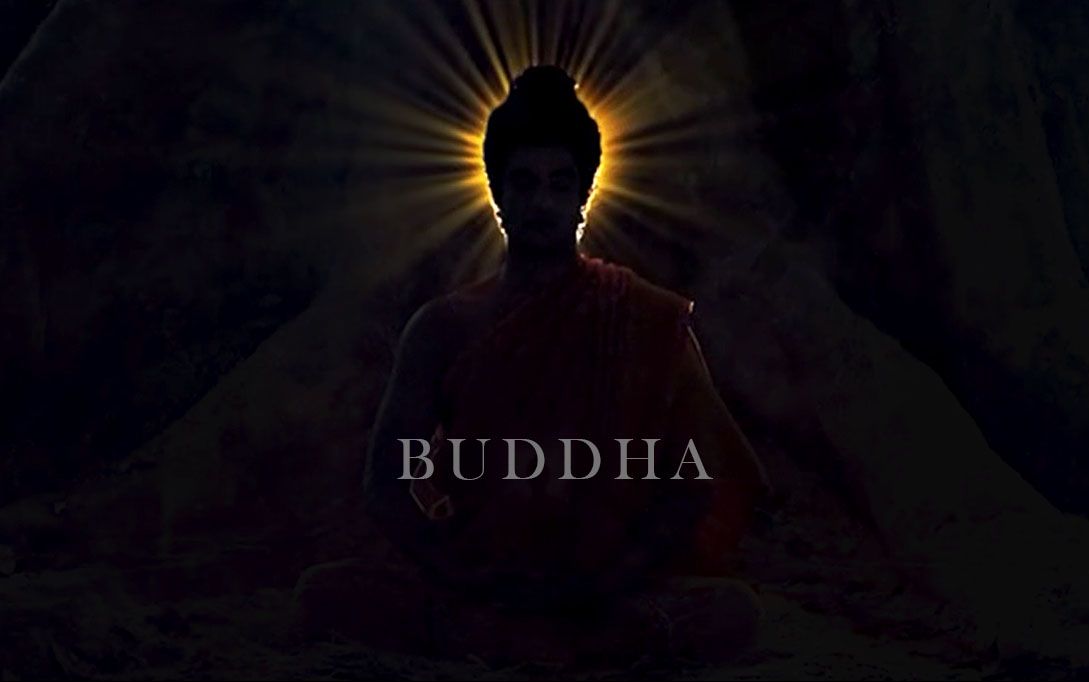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