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如法师:再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第二次佛教中国化略论
三、第二次佛教中国化的序幕
――人间佛教兴起的机与缘
晚清至民国,中国佛教已经沦落为死人的佛教,除了经忏佛事,佛教义学暗淡无光,佛教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大众的正能量也几乎为零。社会大众对于佛教僧团的评价已经从知识精英、文化精英、灵魂导师变为寄生虫!
迫于以上情境,1913年初太虚大师在上海佛教界为释寄禅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佛教革命三大主张’。所谓“佛教革命三大主张”,即是太虚大师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产的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他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卜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的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才,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
印顺法师是继太虚大师之后,在理论上积极推动佛教变革的又一人,他对人间佛教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阐释,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1941年,印顺在其专著《佛在人间》论述到:佛陀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何必执着?是的,不过我们现在人间,我们得认识人间的佛陀。佛陀是人间的,我们要远离拟想,理解佛在人间的确实性,确立起人间正见的佛陀观。佛是即人而成佛的,所以要远离俗见,要探索佛陀的佛格,而作面见佛陀的体验,也就是把握出世(不是天上)正见的佛陀观。这两者的融然无碍,是佛陀观的真相。在大乘佛教的发展中,如果说有依人乘而发趣的大乘,有依天乘而发趣的大乘,那么人间成佛与天上成佛,就是明显的分界线。佛陀怎样被升到天上,我们还得照样欢迎到人间。人间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间,就是天上,此外没有你模棱两可的余地。请熟诵佛陀的圣教,树立你正确的佛陀观: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也’!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人间佛教的迅猛发展,是以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特别是以“成为台湾佛教思想的基调”之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理论为指导的。
继太虚大师以后,如果说印顺法师主要在理论上指导了台湾人间佛教的迅速发展,那么赵朴初先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积极推动了以人间佛教为指导思想的大陆佛教的稳步发展。
赵朴初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明确提出了以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他在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指出:“在当今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赵朴初先生强调,须“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并把它作为中国各级佛协和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指导思想。他把大乘菩萨行作为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把修学菩萨行作为“修行佛道的中心课题”。赵朴初在人间佛教理论基础方面,与太虚大师、印顺法师相一致,都把建立在“五戒”、“十善”基础上的大乘菩萨行作为人间佛教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理论基础,但是他们人间佛教理论的具体内容因时代的变化而存有明显的差异。太虚大师强调人生佛教须与“三民主义”文化相适应,“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赵朴初依据新的时代要求,强调“佛教‘人间净土’的思想同社会主义不矛盾”,人间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因为“佛教的教义告诉我们要‘报国土恩,报众生恩’,要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他明确指出,中国佛教“从整体上和主流上看,它日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扩大开放的重要渠道。总之,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是党和政府可以信赖的同盟者,而不是异己力量。”因此,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不相违背”,“要求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继承先人的遗业,以人间佛教入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可以说,赵朴初的人间佛教,真正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把握了时代的根本精神,切合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为中国佛教的顺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没有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佛教事业的发达”。同时,中国佛教必须积极发挥“人间佛教入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朴老强调,以人间佛教理念为指导的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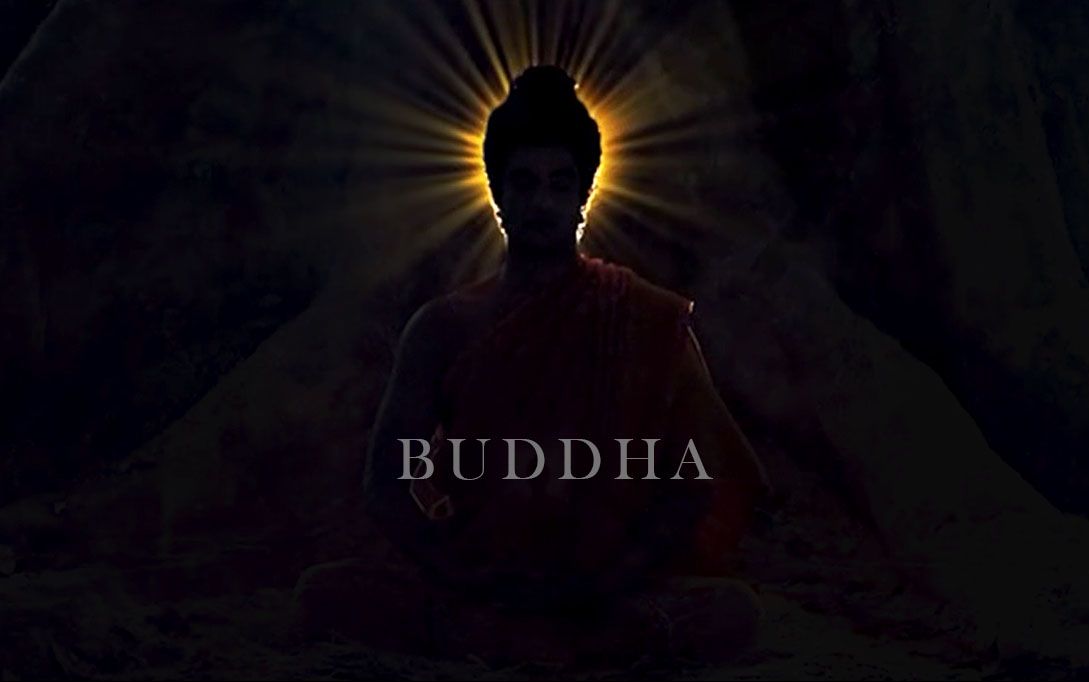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