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钰:汉传佛教祖庭文化与丝绸之路佛教造型艺术
甘肃新疆一带丝路的佛教文化特征与东传的变化
佛教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早在公元前1世纪已陆续从现在的新疆和田(古称于阗),和现在的罗布泊(古称鄯善)等地已盛行起佛教的信仰,新疆现存的以下石窟群便实证了当时的盛况:喀什的三仙洞、温宿的吐和拉克石窟、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新和的吐呼拉克依艮石窟、库车的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玛扎伯哈石窟,焉耆的锡克沁石窟,吐鲁番的雅尔湖、吐峪沟、伯孜克里克、胜金口等石窟。在这些地质条件特定的环境下,新疆天山南麓石窟建造时没有像云岗、龙门那样可雕凿的整块石材,仅是石子状的小型鹅卵石挤压在一块的地质状况而创造的一种既有石窟的传统特征,又有中国人装饰风格纤细表现特征的泥塑处理手法,而且中国人又将绘与塑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敦煌彩塑。
任何艺术、宗教艺术也不能例外,都不能摆脱其民族基本特征,这就和遗传学的DNA一样,自然而然地会传承固有的痕迹,印度人是欧洲雅利安和土著达塞人相融合形成的种族,他们的骨骼与肌肉结构就和中国人有着先天的不同。我可以在印度巴鲁特和桑奇的艺术作品中看到已表现的十分明显,那硕大而坚挺的乳房,纤细而柔软的腰肢,丰腴略凸且脂肪肌肉分明的小腹,粗壮而饱满性感的肥臀,都用石材雕琢的恰到好处,这些药叉的雕像对观众来说,都是一种健美的视觉吸引力,因此印度犍陀罗,秣菟拉的早期佛陀造型上也遗留着这种身材壮实、魁梧的基本身影,直到中国云岗石窟其影响依然可见。
佛教造型艺术从印度步入新疆以后,人物动态先以从原来大的身躯动态中变得缓慢下来,原来性感暴露的躯体,在儒家礼教文化的大环境中减弱了感官的刺激,淡化了性别的特征,特别是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颁布了服装汉化的改革措施,这样一来服装也由于地域气候的变化,而变成了宽松蔽体,数件穿叠,那些异域人形的高额通鼻,低颧骨,薄嘴唇,宽而平的肩膀也都慢慢地通过汉族工匠的创造想象,而变成了道貌岸然超越情欲,超凡脱俗的理想中的神灵形象了。总之在新疆石窟艺术中原有的那些曾经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等文明特质相混合的艺术成分。象印度原有的晕染法,是根据人体的起伏在各个轮廓的边沿部位晕染出体量感(不加同光源光影的心里结构),而各个部位的衔接是以晕染的边沿为界限的,这种方法传到中国后,中国人以自己擅长的线描绘画方法改造了印度的绘画方法,这样一来从白描到平涂填色其速度和效率都比原来的画法进步了,更为重要的是“单线平涂”加强了与西方绘画的差距,突出了东方绘画的装饰性,这也就是西方后期印象派画家梵高临摹日本浮世绘的原因所在,还有线描的表现形式能在整体上统一形式感,这与中国书法的渊源也是十分密切的,因为中国美术水墨中线条自身就是艺术。之所以中国文明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就在于其自身鲜明特征和独立的视觉语言,否则不可能5000多年经久不衰,然而不断交流与发展是其充满青春与活力的“造血细胞”。
佛教绘画的透视构图、题材内容、色彩装饰、人物形象等这些纯视觉的表现形式,在其不同社会背景与经济基础之上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佛教从域外传入,到融入本土习俗之后,原有躯壳尚在,然而其精神内涵方面已完全异化成为另外一种东西的演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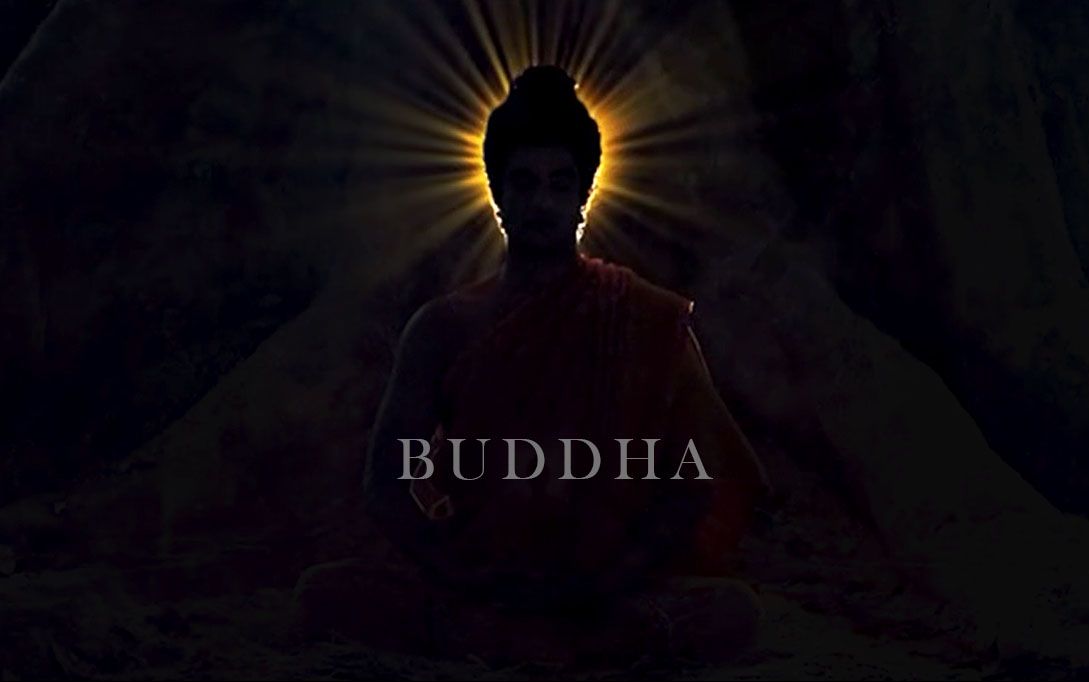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