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恩法师:论灵岩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推动力
宋朝从太宗皇帝开始,帝王与灵岩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灵岩寺现存的辟支佛塔就是宋太宗淳化三年开始重建的。清朝马大相《灵岩志》中记载:“至宋太宗、真宗、仁宗、徽宗,皆赐有御书,奉于阁上。”可惜这些诏书已经没有文字资料可查。
宋朝皇帝对于灵岩寺重大的政治干预发生在熙宁三年(1070)。现存的《敕赐十方灵岩寺碑》完整地记叙了这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当时的住持永义“给府披诉情愿状,退灵岩寺主”。虽然永义法师也是政府派遣,当时灵岩寺僧众不算太多,“有僧行一二百人,遂其四方烧香送供人施利至多。诸处浮浪聚集,兼本寺庄田不少”,但事务繁杂,兼之社会上各种人士“浮浪聚集”,所以寺内很混乱,而永义法师“一向修行戒行”,无有心力管理寺院,所以他向官府请辞。此事反映到朝廷,于是“奉圣旨依奏札付开封府,寻札付左街僧录寺”,左街僧录司智林法师奉旨之后,就选贤举荐“左街定力禅院讲《圆觉经》、赐紫僧行详一名,充齐州灵岩寺主勾当住持”。行详法师在接到委任后,恐独力难撑,又上表要求“指摘僧五七人同共前去充本寺掌事”,即选取五、七有德能的志同道合的僧人一同到灵岩寺担任寺院的职事。虽然如此,行详法师仍然担心灵岩寺的混乱局面难以把控:“行详窃闻,灵岩寺素来最是凶恶,浮浪聚集,前后之六七次,住持不得,虽今来许令指摘掌事僧五七人,亦虑难为照顾。”由此可见当时灵岩寺混乱不堪的局面,所以他又请了一道圣旨:“特乞给一为国焚修传教住持宣札,付身前去,所贵有以弹服远人,废寺易为兴葺,积集功德,上赞圣祚。”他特乞一“为国焚修传教住持宣札”的圣旨,主要目的是借助皇恩国威,“有以弹服远人”,亦即有圣旨在手,可以服众。
于是,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行详禅师带着“护身圣旨”,来到灵岩,慢慢地兴葺废寺。这道敕令,是灵岩寺由废转兴的转折点。可以说,这块《敕赐十方灵岩寺碑》,正是灵岩寺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它再次重启了灵岩寺的历史发展进程。

南宋时期,女真族入侵中原建立了金朝。金世宗曾下诏书保护灵岩寺的山林不受地方的砍伐。其诏曰:“推恩天下山泽,以赐贫民,任其樵者薪之,匠者材焉。惟灵岩同五岳,留护灵脉,不在赐例,采伐者仍治以罪。”
另根据清朝马大相《灵岩志》记载,历史上发现最早的由朝廷明确灵岩寺界域的朝代是在金代,明朝亦曾颁布法令。其文曰:“金明昌中,明成化、万历中,皆见有敕立碑记可考。寺界东至棋子岭,南至明孔山,西至鸡鸣山,北至神宝寺。寺境东西二十里,南北十里。”灵岩寺的田产,于北宋景德年间,在妙空长老的努力下,由朝廷划拨,但之后不断遭到当地豪强的侵占。北宋后期,由金国扶持的刘豫在济南建立了伪齐政权,并于伪齐昌德年间颁布了碑界,但到金代已毁,模糊不可识。灵岩寺现存有金明昌六年(1195)的《灵岩寺田园记》碑,记载了灵岩寺田产的历史由来及当时住持广琛长老多年奔走恢复寺院地产界域的艰辛:“明昌三年,提刑司援他山例,许民采伐,由是长老广琛诉于部于省,才得地之十一二也。五年,琛复走京师诣登闻院,陈词蒙奏,断用阜昌天德所给文字为准,尽付旧地……”
金代不仅保护了灵岩寺的山林田产,还完全免除了灵岩寺的赋税。自此,元、明两朝皆沿袭这一优待。马大相《灵岩志》记载:“赡寺地三十五顷,隋唐以前无碑可考,宋免差徭,只纳税粮,金元明皆奉旨,粮徭全免,至今不税,其籽粒以供本寺香烛之需。”金代对寺院的各种支持,促进了灵岩寺的发展。

五、元代
元代由于蒙古的皇帝皆信奉佛法,元世祖忽必烈就曾下令免除天下寺院的赋税,禁止军民干扰寺院。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来到中国,途经山东临清、济南、东平等地,曾说“所有居民皆是佛教徒”。故在元朝历代帝王的护佑下,灵岩寺的发展一度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元朝历代皇帝对灵岩寺下过的圣旨很多,马大相在《灵岩志》中提到,在清康熙年间“元旨存者尚有八道,盖蒙古风俗,淳朴语言,不尚浮华,大率相同……”
如灵岩寺天王殿东存有一通《元圣旨碑》,刻了两道圣旨,一道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兔儿年颁布,即至元28年(1291);另一道是元成宗在羊儿年颁布,即元贞元年(1295)。这两道圣旨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内容都是对灵岩寺寺产田产的保护。《元圣旨碑》中兔儿年的这道圣旨除了保护灵岩寺的寺产外,还特别提到两点:一是不准官府在寺院内办公及存放公粮,其文曰:“这的每寺院里房屋里使臣每休安下者,不拣是谁,依气力休住坐者,寺院里休断公事者,官粮休囤放者……”二是不仅自此以后免除赋税,还把当地政府催交的鼠儿年以前的税收全部免除,其文曰:“鼠儿年已前的税粮休要者。”
元成宗之后,元武宗即位,他也向灵岩寺特别颁布了与前旨内容相近的圣旨。他的诏书内容在马大相的《灵岩志》中有详细地记载,在此不再赘述。此外,元武宗还于大德十一年(1301),还曾就寺院管理问题向住持古岩长老下诏。
至正元年(1341),元惠宗(即元顺帝,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又颁布圣旨并立《大元国师法旨碑》,此碑现在寺院天王殿东侧,这道圣旨也与《元圣旨碑》上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为了保护灵岩寺的寺产及其发展不受外部力量干扰,同时也要求僧众要安心办道,持戒修行,“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
总之,仅从现存的史料推断,元朝的皇帝对灵岩寺可谓“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关心护持灵岩寺的发展。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灵岩寺在至元年间迎来了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根据《灵岩志》记载,当时寺院占地方圆八十里,聚集僧众二千余人。灵岩寺发展的盛况,也让它一跃成为唐朝以来天下寺院“四绝”之首,这在当时蔡安持的诗中可见一斑:
四绝之中处最先,山围宫殿锁云烟;
当年鹤驭归何处,世上犹传锡杖泉。

六、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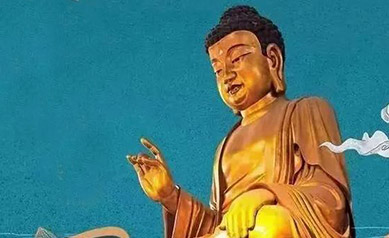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