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耀中:祖庭——佛教中国化的标志及影响
如此特殊的宗教形态之形成,还有着一个由众多因素合成的背景。其中,首先是大乘佛教教义发展的结果,使中国信众普遍地接受了佛性论和轮回说等。自完整的《涅槃经》被汉译后,众生皆有佛性,俱能修佛,成了教界的主要见解。“但众生为惑所覆,如灰覆火,非无火也,乃灰覆故”,于是如何去掉这覆于火上的灰盖就成了修道的关键,也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般的顿悟有了可能。由于这覆火之灰本是自身的惑,所以不能光靠自己去之,非得藉外缘的诱导,即便僧人亦是一样。假如有人帮助掀掉这灰盖,当非师傅莫属,因为师傅是已经觉悟了的过来人,有着助人的能力。所以在禅宗的理论里特别看重师道,可谓事出有因。
与禅宗的情形有某种类似的是密宗,特别是在传授的方式上。因为禅、密之间的共同点之一便是由于对个体身心合一所产生神通的强调,以及在修行过程中师傅对症下药般具体指导的重要性。如此单独指导的唯一性和重要性也不亚于禅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可以说,密宗的修行与传授方式在佛教中助长了禅宗对师承传统之崇尚,它们之间“同大异小现象要比密教与其他诸宗间的关系来得明显”。由于这种传授方式又能够在教派中显示出合法性和正统地位,所以很快被其他诸宗所效法,成为中国佛教里的一个普遍现象。
其次,是和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相关。即“祖宗崇拜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崇拜。它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宗教,发生着持久的并且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影响”。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的是宗族存在的连贯性,祠堂、家谱(族谱)祭祀活动等则是如此传承的具体表现。其中,“祖”的地位是决定性的,因为“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而且这个原则“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被一直延续下来,不可动摇。这种观念当然会影响到在华之佛教,使之将那些能弘扬佛法及本宗教义的高僧尊之为祖,就自然而然了。这证实了如此说法:“不管宗教是(或者不是)其他什麽东西,它都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同其他社会现象处于不断地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中”。如在北朝的造像碑的用语中,“为七世父母”和“为师僧”等词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可以说明两者之间的一种观念交错。佛教中祖庭概念的普及和使用祖庭一词普遍开来是在宋代,这和理学在宋代的兴起在时间上的重合,应该不是出于偶然。因为不仅两者都体现着慎终追远的亲亲之道,也是三教合一的重心在于儒家的模式已经基本形成之影响所致。
祖宗的存在是通过祭祀来确立的,进行祭祖最重要的场所是宗庙。“昔者,先王感时代谢,思亲立庙,曰宗庙。因新物而荐享,以申孝敬”。普通老百姓祭祀祖先的地方叫祠堂,在华夏土地上,凡聚族而居的乡镇村落,几乎都有祠堂,可见这种文化积淀非常之深厚。在中国,除了极少数自天竺或中亚来华的高僧外,僧尼们都是从这个传统的文化信仰里走出来的,潜意识里被留着深深的烙印是无疑的。他们虽然离开了家进入寺院,但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烙印是不会被轻易消退的。
上述两种情况的交叉,对中国佛教存在的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有了祖庭。在佛教进入中国及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高僧大德,是中国佛教兴旺发达的有功之臣。在南北朝之后,以天台宗领先,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诸宗纷纷成立,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还在隋唐期间形成了一个佛学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那些开创一宗之教的高僧,他们要么是一种对佛经所说作出新的诠释之教义,要么是一样新的修行方法,体现着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教义与实践。这些所谓新教义、新修法其实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文化而进行的改变与发展,因此完全可以说尊奉这些高僧的各宗之祖庭孕育着有特色的中国佛教。他们的业绩也完全符合“祖有功”的社会观念,于是他们成为该宗当之无愧的祖师。因此在以他们所属宗派的寺院设立祖师堂以供奉之,也完全符合情理,因为本身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宗教,不可能与它的背景文化相隔绝。而那些祖师曾经驻锡、讲法过的寺院当然进一步升格为祖庭了。同一文化相连的道理,祖师堂和祖庭在佛教中的地位,尤其是在诸宗中的地位,犹如世俗社会里的太庙与祠堂,在各个宗派的僧团里起着无可替代的凝聚力的作用。而`这样子一个师徒传授使得法统义学绵绵不绝之宗教形态,无论在教内还是教外都是非常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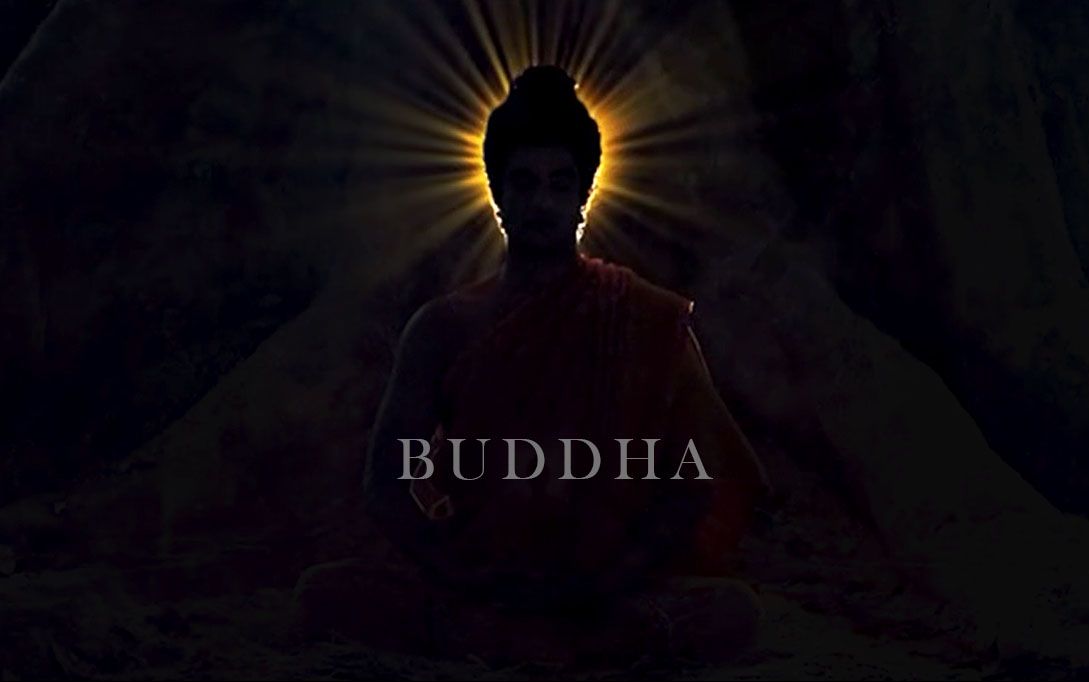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