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伟:天台“圆教”与隋唐帝国“意识形态”
确立“圆教”之“礼”(礼法)为本经之“正体”,而以圆融三谛方为诸法之“结构性”所在,如此,行人“修行”之“场域”即无有限制,而可即就“一切法”,所谓“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就将“佛教”之职能范围由特殊性之“出世间法”领域,扩展至一般之“世间法”领域。如此,从佛教“自行”与“化他”之关系来说,就不是机械地以“自行”为“实”,“化他”为“权”,而是表现为一可“诠释”性。即如智者大师所云,“既不会正体摄属何法,但空是化他之实,但不但是自行化他之实,出二边中是自行之权,并他经所说,非今体也。今经体者,体化他之权实即是自行之权实,如垢衣内身实是长者;体自行化他之权实即是自行之权实,如衣内系珠即无价宝也;自行之权即自行之实,如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况自行之实而非实耶”。《法华》经本以“佛”之“知见”为“自行”之“实”,以种种善巧方便为“化他”之“权”,“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就是要藉“权”而入“实”,故自行/化他尚有实/权之对立。而经智者大师之诠释,自行/化他关系转为“自行”对“法性”的不同通达状态。这样,作为“佛”之“化他”手段的“治生产业”可以充任“众生”之“自行”,所谓“自行之权即自行之实,如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
这样一种表述,其实也就将佛/生并置于同一场域空间,由此二者之别不再是“听说”角色之异,但在于对“治生产业”之“结构性”的通达程度而已。换言之,“佛”可以而且必须“介入”到“一切世间治生产业”中。因为众生虽“处于”“一切世间治生产业”中,然其不“自觉”,未能了达诸法之“体”。故此“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之命题,其之表述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说明了世间之人可藉“世间行为”而通达“实相”,此是对传统佛教承担“出世间法”职能“特权”的一种“放弃”;而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对这种“特权”“放弃”,佛教反而扩大了其“权能”,得以更普遍的“礼法”身份参与到世俗社会中。就此,我们或许可以在一更高的思想层面上把握智者大师与时为晋王的杨广之互动关系,杨广尊智者大师为师,极尽弟子之礼,而智者则为其授菩萨戒,二者之间虽存有一紧张博弈关系,不可否认正是通过此一博弈,天台宗得以获得中央王权的支持,从而在隋代有一特别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天台“圆教”之建设实是佛教应对新兴帝国政治格局之表现。在对传统佛教予以重新系统化的组织、诠释的基础上,天台宗将佛教由一特殊性之“出世间法”发展为一普遍之“礼法”,从而承担其帝国意识形态之角色,为隋唐制度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原标题:天台“圆教”与帝国“意识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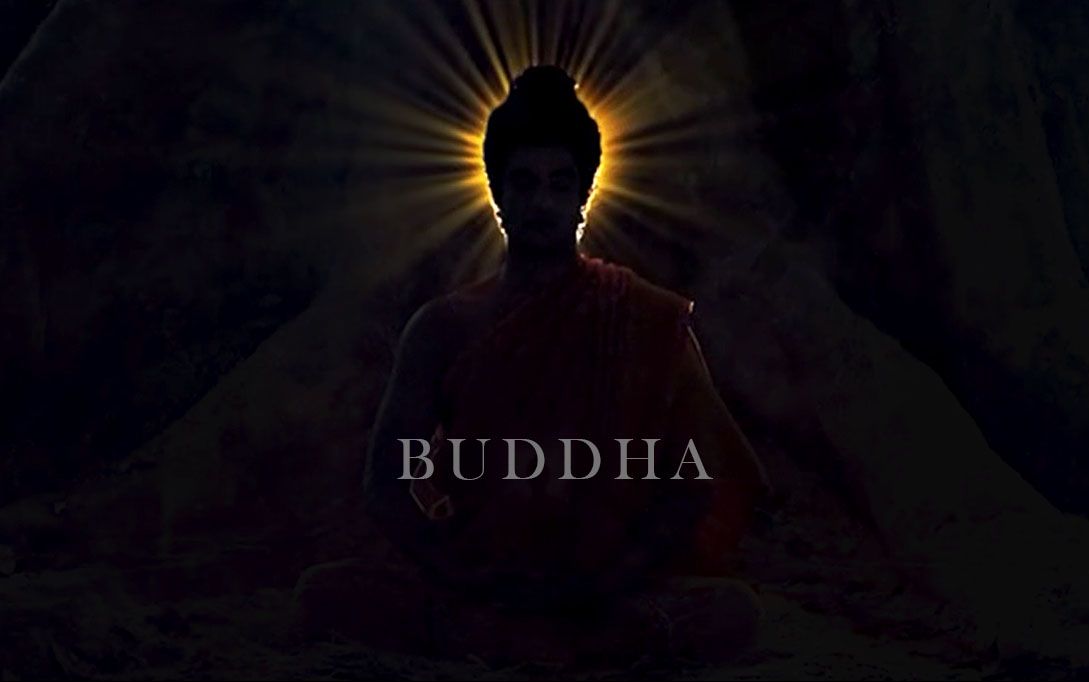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