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伟:天台“圆教”与隋唐帝国“意识形态”
自然,一般所云之“世间法”只是“泛指”,并没有一特别明确之所指,而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世间法”即等同于儒家名教“礼法”,成为一“定指”。将世间法/出世间法对置为儒家礼法/佛教之关系,这是东晋佛学大师庐山慧远特别的思想贡献。在其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中,针对世俗人士的质疑,慧远提出了世间法/出世间法分别,申诉了释子豁免行世俗礼法之理由。所谓“法”,其实就是广义之“礼法”,世间法也就是指规范世俗之人的礼法,至于出世间法则是修行清净解脱者的礼法。慧远承认世俗之人(包括在家居士)必须恪守世间礼法,原因在于,世俗之人乃是顺化之民,故求“厚身存身”,既处“自然”状态,则父母双亲之恩爱、君王人主之资养不可忘,未可“受其德而遣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故要求忠孝敬拜。至于出世间法,乃是作为方外之宾的职守原则,而不同于世俗之人所守之礼教。因为出家人乃是“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非是顺化之人,故不贵厚生,不重运通。释子身份既不同世俗之人,其职守但在于息患达道,故其不得同礼世典。虽然出家者不服世法,然其必须守“出世间法”,所以慧远并没有否定职守/礼教之对应关系,恰恰要根据不同层次严格地恪守礼法原则。同时,故较诸魏晋名士的不拘礼教,作为方外之人的慧远倒是确立了世俗之人与世间礼教的对应关系,重新恢复了名教的合法性。如是,通过出家而求解脱,慧远在更高层面调停了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矛盾,从而开拓了士人生命更大的可能性。
显然,庐山慧远对世间法/出世间法关系的说明指示了,虽然出世间法高于世间法之层次,然二者各有权限,不可淆乱;即便前者能够“迂回”地“裨助教化”,间接地履行“世间法”之职能,然二者之畔域界限是分明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六朝时期虽三教论衡,互有攻伐,然各教甘于自身之特殊性身份职能,并不希冀有一更高层次的身份职能追求。这种情况到了隋唐帝国时代,即发生转变。如前所述,帝国政治之维持需要一普遍之意识形态学说之支持,故宗派佛学的兴起乃是契合此一时代,不过佛教既然要承担一普遍意识形态之职能,则其就不能甘居特殊性的“出世间法”之身份,而必须扩大其身份职能。为此,宗派佛学之给出“判教”,乃是藉“判释”“佛”之“言说”的形式,重新整理、组织佛教,从而确立一“新”的佛教形态,“圆教”正是此一佛教新形态的表现。不过,“圆教”既然是要承担一普遍性之意识形态职能,则所谓“圆教”就不惟局限是在佛教内部而言,实应理解为是在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上的一个“教法”。正如宋明理学(新儒学)乃是儒家吸纳佛道因素,将既往之儒家“礼学”扩展为普遍性的“理学”一样,隋唐宗派佛学之“圆教”则是佛教吸收儒学(包括道家)因素,将“出世间法”的佛教扩展为一“圆融”性的“佛教”,亦可云是一“普遍”性的“礼法”。那么“佛教”作为这一普遍性之“礼法”,其理据何在呢?对此,智者大师提出了一切存有之法不出“法性”(实相),当依“实相”为“体”(礼)的思想,从而给出了最有理论价值的说明。
“诸法实相”概念乃出于《法华经》,本指众生果报境界之种种方面的表现,所谓“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由于“佛”之知见“广大深远”,能了知、究竟此种种境界,故其得以应众生之“性欲”,开示种种“善巧”方便。虽然“佛”之知见非众生所能知,然“佛”之开示《法华经》的目的正在于令众生“了知”、“悟入”“佛”之知见。可见,在《法华》经典文本中,“诸法实相”乃是基于佛/生之“言教”关系,特指众生“果报境界”之表现,以相应说明“佛”之化他能力,而并无理体原则之抽象义。即至《法华玄义》,智者大师乃将“诸法实相”抽象化为一“理体”(法性)概念,用以解说“存有”之“法”的“体性”。故在以“五重玄义”之“辨体”解释《法华经》“经体”时,智者大师说道,“体字训礼,礼,法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君臣撙节。若无礼者,则非法也。出世法体亦复如是,善恶凡圣菩萨佛,一切不出法性,正指实相以为正体也”。在此,智者大师将“体”视为“礼”,即一套礼法规范,其借世间法说明,世间行为需要以儒家纲常名教之“礼”规范、节制之,同样,出世间行为亦需要相应之“礼法”规范,此一“礼法”即是“法性”(实相)。事实上,智者大师不惟以“法性”为出世间行为之“礼法”,且是世间、出世间一切“存有”之“法”的“礼法”,所谓“一切不出法性”。“法性”既为“一切法”之“礼”(体),则既往所谓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差异、对立也就由一“外在”性,转变为一“内在”性。换言之,判别世间法/出世间法的最终根据不在“行人”之“身份”,而在“行人”对“法性”之了达程度。故如其云,“故《寿量品》云:不如三界见于三界,非如非异。若三界人见三界为异,二乘人见三界为如,菩萨人见三界亦如亦异,佛见三界非如非异,双照如异。今取佛所见为实相正体也”。显然,同见“三界”之法,由于“行人”对“法性”的了达程度有异,故有不同之知见境界。进言之,行人“见”的层次与“见”相应“法性”的程度是一致的,“见”愈受“法性”之“规范”,则也就愈照见“法性”。以“法性”(实相)为存有之法的“法体”,其实也就是要揭示“诸法”的空假中三谛“结构性”,不过隔历三谛尚为“粗法”,非“究竟”实相,圆融三谛方为“妙法”、“究竟”实相。故从这个视角看,藏通别圆四教之次第给出乃是相对于“三界之人”的“世间法”,“但空”、“不但空”指藏、通二教,“但中”、“不但中”则为“别教‘、“圆教”,此一层级推进正说明,“圆教”之“礼”(礼法)乃为本经“正体”,行人当依此“体”(礼法)而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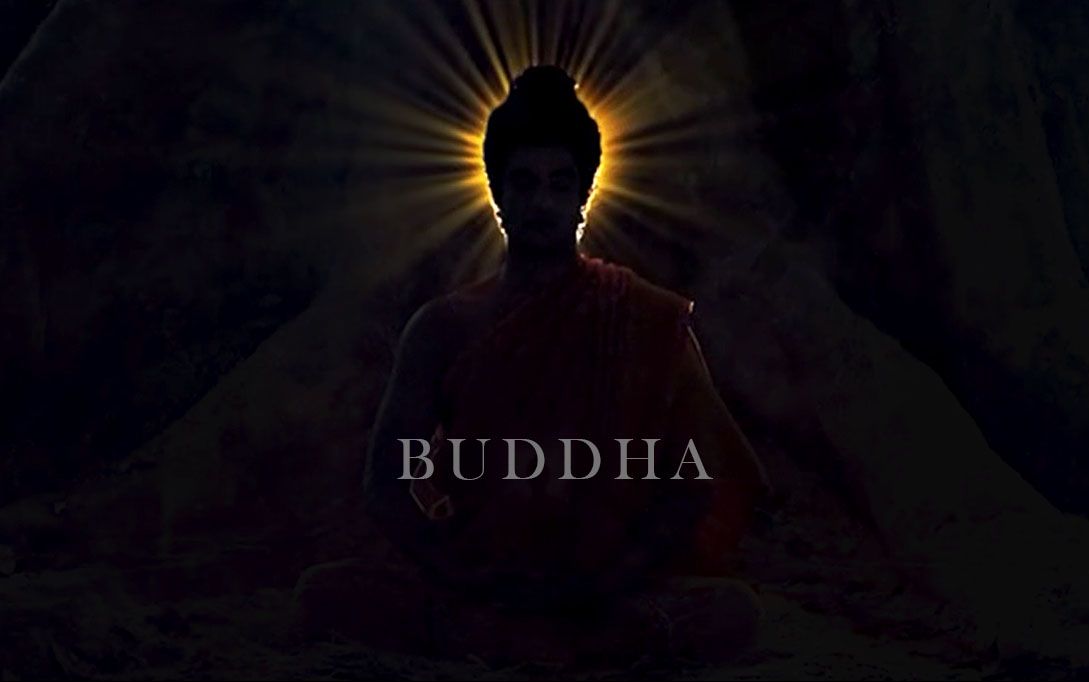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