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伟:天台“圆教”与隋唐帝国“意识形态”
隋唐宗派佛学既为隋唐帝国之精神总纲,故其学说体系建设表现出相当大的创造性,此主要体现在:以台贤为代表的隋唐宗派佛学在理论构建上博大而涵容,能够将种种差异的思想因素予以调停整合,将之纳入到一个据于自身立场的更大的思想形式中。为此,相对于六朝学派佛学,隋唐宗派佛学均有一自觉的树立己派“宗旨”的意识,并在理论上将之合法化,此特别表现为通过判教形式来确立本宗的“圆教”地位。从形式上看,隋唐佛学之判教乃是依循佛教经典为佛之方便说法之事实,对东传汉地之佛典全体予以高下权实之判释,以确立最终究竟之说的经典所在;而实质上,判教乃是不同宗派依据自身的思想立场,藉对既有佛教之诠释来安立本宗学说的最高地位。故相对于六朝佛学之“照着”说,隋唐宗派佛学不是围绕“梵胡经典”翻译展开文本疏义,而是依托某部经典而申发义旨,确立其新说,故乃是“接着”说。由于隋唐宗派佛学成立于不同“判教”体系的建立,故宗派论辩亦主要围绕“判教”体系展开。因为不同宗派尤其是台贤二宗,其“判教”之给出意在确立各自的“圆教”地位。“圆教”意味着最圆融的“教法”,故有其至高的尊贵性、权威性,但“圆教”其实不是从“佛说”之脉络给出,并非是对“佛”之言教史“事实”的认定,而实是中国佛教思想家一当下性的思考,是对“佛教”所作的“思想形态”构拟。换言之,“圆教”并非只是所谓佛教的某一特别或最高阶段性之教法,而乃是隋唐佛教大师给出的“唯一”有效的、合法的佛教新形态;从形式上看,“圆教”乃是佛教内部“协议”的结果,只是要解决佛教自身教法差异性的问题,而实质则是佛教学者为应对新的帝国政治形式,藉对传统佛教形态的“反思”、“批判”、“整合”,解决佛教存在的合法性危机,进而转型、扩展为一普遍的意识形态。因此,佛教判教之目的在于对佛教自身作一反思性处理,以便以一新形态的形式定位佛教,确立其职能所在,而“圆教”实际只是此佛教新形态的代名词而已。至于为何要以“圆教”之名来表说之,原因在于,“圆”既意指圆融、圆通,则“圆教”即谓“圆融至极”之“教”,以至于,其不惟是局限于“佛教”内部范围的“佛说”之“言教”,而是在更广大范围内的调停世间法/出世间法之“教”。由此,佛教才能以一普遍学说的身份,“充任”帝国意识形态的职能。天台宗之“圆教”之设意在此也。
二世间法/出世间法的调停:一切不出“法性”
如上所述,智者大师既给出一“普遍性”之“圆教”,则此“圆教”虽仍隶属于“佛教”,然已超出了佛教原有之身份范围,从而获得了一更大之职能。具体来说,原有佛教之身份乃是所谓“出世间法”,而有别作为“世间法”的儒家“礼法”;至于作为“圆教”的“新佛教”,则不自限于一“出世间法”身份,而是由“出世间法”扩展为一更为普遍的“礼法”,从而在更高层面上调停了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对立。从理论上讲,“圆教”取得此一身份职能之依据在于,一切法“不出”法性,均以“实相”为“体”(礼)。
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一般来说,从佛教之角度讲,“世间法”是指维护基于“我执”之世俗生活形式的制度规范乃至价值观念,出世间法则反之。早期佛教虽然出自“沙门“思潮,然其最终扭转“沙门”外道“禁欲苦修”之修证方式,而示以“八正道”之“中道”之行,开启“智慧解脱”之门。故佛教虽然自命为出世间法,只是“弃舍”世间生活的“染污”成分,而非全盘否定“世间”生活。因此,当代“人间佛教”的提倡者印顺法师再三强调,佛陀修行、证悟、教化均在“人间”;而现代“菩萨乘”论的提出者吕澂居士亦特别区别了佛教之声闻乘/菩萨乘,指出佛教“出世”修行之根本在于“转化”染著世间,所谓“即世而转世”。凡此这些申明乃是要说明,佛教虽有“出世间法”之名,并非是“消极”避世,而有其“转化”世间的积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虽名“出世间法”,而并不完全与“世间法”对立,其可在更高层面上承担“世间法”之职能。所以从狭义上讲,“佛教”之“出世间法”乃是对立于“世间法”,是否定作为维护“我执”生活形式的制度规范,然从广义上看,“佛教”之“出世间法”隐含了一更高层面之“世间法”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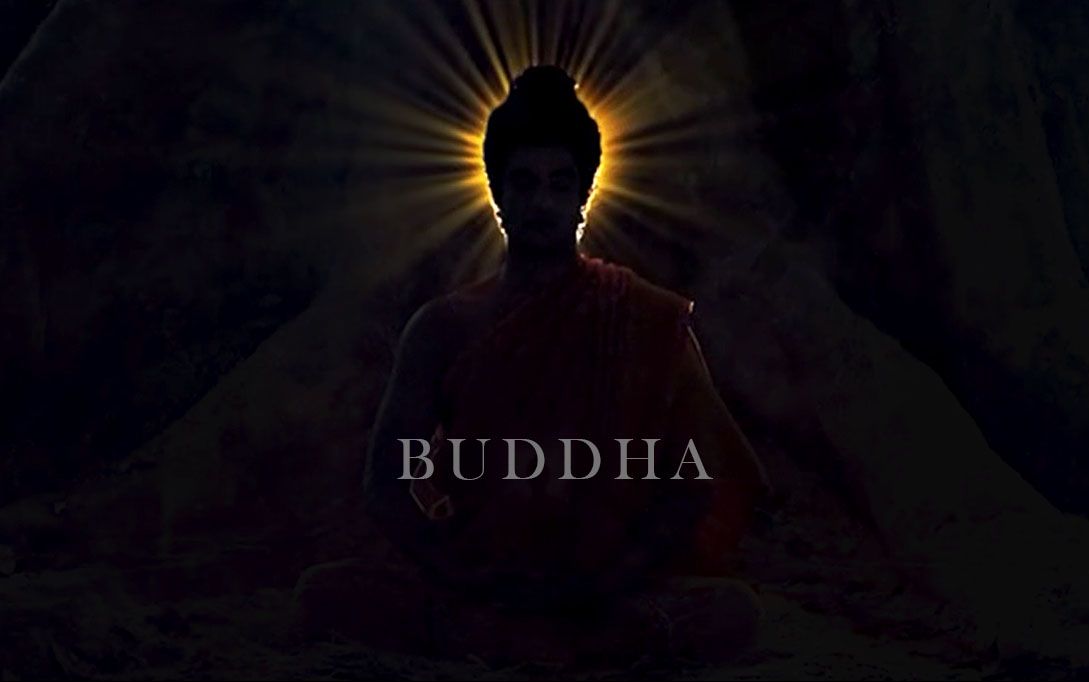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