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的宗教信仰与戒杀放生实践
宋代士大夫所作有关戒杀放生的诗文很多,本文考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北宋初王随作有《杭州放生池记》,论及当时朝廷上下的“戒杀”理念,谓“皇帝仁及万有,惠济群品,法神武之不杀,守慈俭以为宝。奏牍诚激,凝旒喜动,濬发中旨,普令茂育。丝纶适降,已改观于方塘;罔罟靡施,免有叹于頳尾。既厚生生之乐,永焕巍巍之业。”文末列知钱塘县事杨告等二十余名官僚职务、姓名,可知建立杭州放生池不仅关乎个人信仰,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甚至称得上一种“官方行为”。
陈舜俞《施食放生文》尽管是一篇仪轨文字,但也揭示了佛教放生的本质含意:佛教的生命观面对的是六道中一切众生,救度众生的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动物,还包括饿鬼道等人类看不到的众生,因而放生与施食往往同时进行,令“一切饿鬼、水陆空等皆得饱满,一切畜生、羽毛鳞甲类皆得自在。”
南宋初士大夫陈录在其所作善书《善诱文》中记载:
苏东坡自谓:窜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颇忧之,愿学寿禅师放生,以证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尽买放生,以荐父母冥福。其子迈在东坡之侧,见所买放生盈轩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鸣。迈怜悲其意,亟请放之。旁有侍妾名朝云,见迈衣衿有蝡动,视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陨其命,东坡训之曰:“圣人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我今远取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诸身以杀之耶!”妾曰:“奈啮我何?”东坡曰:“是汝气体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当拾而放之可也。今人杀害禽鱼之命,是岂禽鱼啮人耶?”妾大悟。
相当生动地写出苏轼晚年对戒杀放生的重视。《善诱文》中还有多则文字都是有关戒杀放生,堪称一部“戒杀事迹汇编”,其宗教意义相当明显。苏轼《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其一似可印证《善诱文》所记应该是有根据的:
左角看破楚,南柯闻长滕。
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
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诗中表示自己甘愿做一个持守戒律,能够做到“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的小乘僧,颇能显示作此组诗时晚年的苏轼对佛法的真诚信仰。苏轼还有《次韵潜师放鱼》诗,也是写放生的:
法师说法临泗水,无数天花随麈尾。
劝将净业种西方,莫待梦中呼起起。
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
况逢孟简对卢仝,不怕校人欺子美。
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
法师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
道潜原诗题为《虚白斋》:“与子瞻共坐,有客馈鱼于子瞻,瞻遣放之,遂命赋是诗:嘉鱼满盘初出水,尚有青萍点红尾。银腮戢戢畏烹煎,倔强有时俄自起。彼客殷勤赠使君,愿向中厨荐醪醴。使君事道不事腹,杞菊终年食甘美。传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边放清泚。回首无欺子产淳,谩道悠然泳波底。”(《参寥子诗集》卷二)苏轼的次韵之作则通过几则与烹鱼、放鱼有关的典故,进一步联想到所治百姓如网中鱼般备受折磨,体现出一种众生同体的悲悯,主题也显得更为深刻。
陈录《善诱文》记有苏轼与黄庭坚一番对话:
黄鲁直谓子瞻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某适到市桥,见生鹅系足在地,鸣叫不已,得非哀祈于我耶?”子瞻曰:“某昨日买十鸠,中有四活,即放之,余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买鱼数斤,以水养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悦我口。虽腥膻之欲,未能尽断,且一时从权耳。”鲁直曰:“吾兄从权之说善哉!”鲁直因作颂曰:“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元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须。莫叫阎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闻斯语,愀然叹曰:“我犹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阎老之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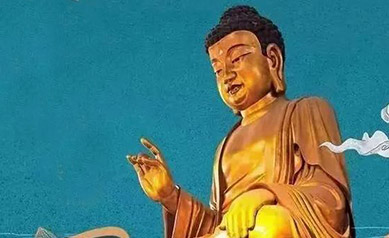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