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的宗教信仰与戒杀放生实践
这段记载颇有小说味道,未必完全属实,但记苏黄二人晚年心态颇为亲切,并论及戒杀的“从权”问题,应该是有一定真实性。
北宋晚期士大夫龚夬,字彦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举进士,签书河阳判官等职。宋徽宗时,拜殿中侍御史,《宋史》卷三百四十六有传。这样一位士大夫对于佛教的信仰极为虔诚。《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九引《冷斋夜话》谓:
龚彦和谪化州,持不杀戒。日夜礼佛,对客虮虱满衣领,不恤也。邹至完作偈嘲之,曰:“衣领从教虱子缘,夜深拜得席儿穿。道乡活计君知否?饥即须餐困是眠。”(《诗话总龟》前集,380页)
邹浩本身即是对佛教有深厚信仰的士大夫,但所学以禅宗为本。可能连他也认为龚夬的“持不杀戒”做得有些过分,故作诗讥讽,希望他以平常心学佛,即诗的最后一句“饥即须餐困是眠”。此例或许可见宋代士大夫对于持守戒律的不同态度。
在主张戒杀方面,曾任南剑州顺昌县令的俞伟更是不遗余力。俞伟,字仲宽,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元祐初,为南剑州顺昌县令。《善诱文》一书收有俞伟三篇有关戒杀的文章,如《人与物同》谓:
贪生畏死,人与物同也;爱恋亲属,人与物同也;当杀戮而痛苦,人与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则无智;人能言,物则不能言;人之力强,物之力则微弱。人以其无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诉,以其力之微弱,不能胜我,因谓物之受生,与我轻重不等,遂杀而食之。凡一饮一食,不得肉则不美,至于办一食,又不止杀一物也。食鸠鸽雀者,杀十余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虾蚬者,杀百余命方得一羹。又有好美味求适意者,则不止据现在之物,顺平常之理,杀而食之。或驱役奴隶,远致异品;或畜养鷄鱼犬彘,择肥而旋杀。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鱼造脍,欲有经纹。聚炭烧蚌,环火逼羊,开腹取胎,刺喉沥血,作计烹煎,巧意斗飣。食之既饱,则扬扬自得,少不如意,则怒骂庖者。嗟乎!染习成俗,见闻久惯,以为饮食合当如此,而不以为怪。深思痛念,良可惊惧。县令俞伟撰。
将杀生之恶写得惊心动魄,读来令人心动。《善诱文》还举出若干当代士大夫的实例以证明“有生爱恋,其情如此”之理:“近者,沈遇内翰通判江宁府时,厨中杀羊,屡失其刀,窥之,乃见羊衔刀而藏之墙下。周豫学士尝煮鳝,见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汤者,剖之,见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汤者,以爱子之故。杨杰提刑游明州育王山,因昼卧,梦有妇女十数人,执纸若有所诉,密遣人往视行厨,果得蛤蜊十数枚,诉者,乃蛤蜊求生也。”(《全宋笔记》第七编第2册,61页)要之,《善诱文》这部宋代士大夫编撰的劝善书,对于戒杀的记载尤为详尽,确实是将其视为天下“第一善事”。
吕本中的八首《戒杀》诗也集中体现着宋代士大夫有关戒杀的种种心态和观念。
其一
劝君勿杀犬,犬有为主心。
为主反见杀,君何无浅深。
君贫犬不去,君富犬分忧。
执以付鼎镬,于君心稳不?
其二
畜犬被缚时,犹为主人吠。
吠声不绝口,汤沸主已退。
主人调醯盐,欲以佐滋味。
持此望身安,世间宁有是。
其三
犬虽有小过,未至不得活。
卖钱与屠宰,使得恣脔割。
君儿小不安,君夜不得眠。
何独于此犬,如此安忍然。
其四
劝君勿杀鸡,鸡能伺昏晓。
闻鸡君即起,一一家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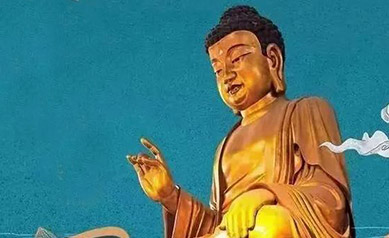















 关于中华网
关于中华网